从香港离开的内地生们:墙根下的人

“我只能抛弃媒体那些解读,自己看视频尝试去感受那个真相。但你感受到的也不是真相,就是不好说。你没有途径去了解真相,了解了你也做不了任何事。”
“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表港中大内地生发表任何观点。我们只是整场风暴中的旁观者,我们才是受害者,而旁观却成了一种罪。”
“即使了解了他们的想法还是会反对他们,他们的行为逐渐把我们推向了他们的对立面。”
“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梳理得很清楚,混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当你无法像日程计划表一样厘清每件事的时候,混沌就接受混沌吧。”
“我是一个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人,我来香港只是为了学习拿个学位,在他们真正影响到我之前我完全不关心发生了什么。”
那天
曾鸣一开始听说“三罢”消息的时候没有很在意。从今年9月开学到现在,这样的事情他经历了不少了,他想可能只是正常的停一天课。
2019年11月11日,周一,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大六的内地生曾鸣今天没课,他一天都呆在寝室里。从他寝室的窗口可以看到整片操场和对面的二号桥——警察和示威者的对峙就发生在桥上。周二下午,曾明发现学校的气氛有些不对了,对峙向操场蔓延,双方的催泪弹和燃烧瓶扔在了操场上,零散的一些黑衣人在操场上奔走。
窗外,黑烟和白烟在两处同时升起。一辆车被示威者点燃了,隔着操场曾鸣可以闻到催泪弹的味道。
他听说导火索是周一晚上示威者开始往二号桥下的公路投掷物品,可能会阻碍公共交通、砸中车辆,于是警方开始了对那座桥的争夺。

看到窗外的景象,他感觉情况不是很安全,今年10月,因为在窗外挂国旗,他的寝室在Facebook上被人起底过。他想暂时到深圳去避几天,晚上七八点,他和朋友约好一起离开了学校。在内地生的交流群里,他知道学校前面的几个路口都被封了,还剩下学校后面和平时不常走的出入口。
他是港中大最早几批走的人,和朋友在自己订的酒店里住了几天。11月13日,港中大宣布学期结束,公告中没有对课程、考核等后续安排的说明。港中大深圳校区自发向前来避难的同学提供宿舍,曾鸣提供了学生证和证明身份的文件,就在宿舍里又住了下来。
来到深圳以后,他听香港本地朋友说,聚集在港中大校园里的主要已经不是学生了,是外面进来的团体。一部分的学生宿舍被他们“征用”来作储存物资和休息的地方。有市民自发每天给他们提供一百多份叉烧饭,有时候吃不完就在群里问有没有谁要吃。
周一从宿舍下山前,港中大大四内地生徐静怡不知道任何消息,下山路上她看到】一个外国教授很生气地和一个本地人争论,说着什么无法出行。
她今天要去九龙参加一个面试,七点半出门后发现地铁站关了,附近也坐不上什么巴士,她转身回了宿舍。她想第二天应该就好了,于是把面试往后推了一天。
第二天她早了一点出门,结果地铁又关了。徐静怡穿着正装一个人走下山,路上经过了两队黑衣人,他们“全副武装”,拿着垃圾桶和雨伞,没有人理她。她随便坐上了一辆不知道去哪的巴士,倒了两个小时到了面试的地方。
面试完,她觉得学校可能回不去了,买了周五回家的机票,到一个在外租房的朋友家借宿。晚上,一个朋友在港中大内地生里做了一个小型统计,大概有一半的人已经回深圳了,有五分之二的人准备回去。她把机票改签到周三。
借宿的朋友家在香港大学附近,徐静怡感觉港大一片平静,在港中大宿舍,早上七点她就会被警笛吵醒。
对港大大一内地生秦乐博来说,11月11日前的周日还很和谐。他们宿舍楼正在办一个美食文化活动,他和同学做了一些上海菜,邀请了楼旁公屋的香港老人一起来吃。周日下午,秦乐博看到了示威者要发起“和你suck”活动的消息。一个学长就和他商量说,“他们塞我就早起”。
周一,秦乐博和学长五点起床乘第一班地铁到了学校,港大和他的宿舍相距一站。他坐在图书馆外的椅子上等九点半的课,大概七八点,一队队黑衣人开始从他身边匆匆忙忙走过,离他很近。他们拆下人行道护栏或者搬出课桌椅摆成路障,挡住学校的出入口。
他陆陆续续听到同学进不了学校的消息,但校园里还是很平静。他抱着可能上不了课的希望走进教室,却发现两百人的课还是有七八十人到了,大部分是内地生。当最后教授走进教室的时候,教室里的同学都鼓起了掌。
港大在中午发布了周一停课的通知,这是秦乐博印象里港大第一次在周中停课。他还是在食堂吃了饭,同学告诉他警察和示威者已经在学校的两个口对峙了,校园里也被扔了些催泪弹。吃完饭,他和同学从隐蔽的口离开学校,经过文娱中心的时候里面黑压压都是黑衣人,他和同学说着普通话经过,还跨过了在地上躺着的黑衣人,什么也没发生。
回寝室的路上,秦乐博第一次见到街上有这么多救护车和警车,他觉得救护车比警车更多。
之后的两天他在寝室里一遍遍改自己关于荷兰画家的作业。到周三晚上,他妈妈说给他订了机票,他突然发现周围的同学都走了。第二天早上,他坐上了回家的飞机。港大在11月14日宣布了学期结束,课程都改成网上授课形式。但到了17日,秦乐博觉得还是处于“一团乱麻”的状态,他去问一节课的助教一个上周四该交的作业什么时候要交,助教说十分欣赏他的态度,但还是没有一个商定的时间。
秦乐博记得港大只有周一那天有警察和示威者的对峙,之后警察就撤走了。他有看过一张照片,照片上两个示威者躺在草地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
香港每所大学的实际情况都不一样。
香港理工大学的内地生刘一城11日早上醒来就看到了邮箱里学校的停课通知。他就打开“香港01”看一些校园情况的直播,那天早上好像其他学校“都还好”,理大里的示威者已经开始燃烧一些垃圾桶,砸毁星巴克、美心的店铺。之后,停课通知一天一天地发布,他就在宿舍呆了两天半。
刘一城的宿舍在校园外。他觉得宿舍周围很平静,不担心安全问题,只是交通瘫痪了,也会被外部环境干扰,没法很专注地学习。所以他和室友打算到深圳先避几天,在周三已经有了一些针对在港内地生的救援团体,他在省青年会的群里只问了两句,青年会的人就告诉他已经安排好了深圳的酒店。他感觉“效率很高”,“有种背后有人支持的感觉”。
香港浸会大学的内地生张欢乐在11日前的整个周末都在赶一篇周一要交的论文。她没看任何新闻,周一突然收到学校的停课通知,她感到有些恍惚。这时候她才开始看新闻,觉得一夜之间变了好多。
刚刚结束期中季,又停了课,张欢乐没什么事做,周二她就到浸大附近的又一城逛街,那是九龙比较大型的一个商场。到了又一城,她发现大部分的商店都关门了,她从来没见过商场里的人这么少。
晚上回来她看到了又一城的圣诞树被烧的新闻,那棵中庭的圣诞树有三四层楼那么高。她又看到那晚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性事件,她突然意识到肯定明天也上不了课了,她开始打算第二天回深圳。
离开香港后,她看到香港本地朋友分享的一些照片,从周一开始学校里就基本清空了,很多地砖都被翘起来,在学校附近的主干道联合道上摆成石墩。“很像反乌托邦电影里的场景。”
风暴之间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张欢乐和她的室友们都已经习惯了一种“固定模式”:从周五下午开始到整个周末,示威者都会有游行活动,有些时候周一也会有游行,就会没法上班。
示威活动不大会影响到她们的正常生活,只要在出行前看好示威者在网上发布的信息,避开会有游行集会的场所,或者避开港铁坐巴士去学校,“暴力的冲突都是发生在最前线的。”
所以11月11日之后发生的事让张欢乐感到十分突然。其他在港内地生也和张欢乐一样处在一个突发的状况中。
余滴是港中大大二的内地生。她有同学在拉着箱子从学校逃离的途中,被旁边的黑衣人指责“快滚回去”,箱子被黑衣人踢到。
而回到内地,当余滴试图跟身边的人解释香港复杂的情况时,她又被说是“被洗脑”的人。
港大大四内地生林峰看到知乎上一边倒的言论也同样在指责内地生。他感到“非常愤怒”。他觉得示威者们让他们没法留在香港,而内地对香港的印象变差又影响到了他们。“他们整场行动中,我们是最大的受害者,所以不可能支持他们。”
徐静怡觉得在港内地生仿佛是“生活在夹缝中”的一群人。
“我们内地生自己的情绪目前也不是很稳定很冷静。”曾鸣记得最初的一两天,他朋友圈里的大部分内地生都在说着“香港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们学校遭到了很严重的破坏”,表达谴责和担心。
但当有媒体“夸大报道”香港校园里的情况后,他朋友圈的内地生转向辩解说学校里的情况其实没那么糟。而这一“转向”又被媒体“断章取义”,就会有人举报公众号、和媒体对骂,有人出来让大家冷静,过两天又去骂另一个公众号。
刘一城说:“我们处在这个事件的风暴中心,不一定会很理智的,有时候真的是为了我们的利益着想,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他补充说:“据我所知,我身边的内地生没有一个是不爱国的。”
多种不被接纳的感受都被表达为一种身处“夹缝”的感觉。
秦乐博在今年8月真正来到香港后,才慢慢发现之前在内地接收到的关于香港的事实“甚至没有10%”。他感觉自己在尽力往另一边看,可能自己也不能被另一边接纳,只是往那边看了以后,他也很难回到现在所处的这一边了,“就感觉像在一个夹缝里一样”。
11日之后,港中大内地本科生联会会长两天没睡,帮助内地生们四处协调离开香港的车辆。港中大大四内地生郭涛涛说,内地生在港校学生中的比例是相当小的,所以内地生在校学生会里也占不到很大的比例,学生会不会去考虑在港内地生的诉求,他们只能“抱团”组建了自己的联会。
港中大本科生联会在11月15日发布了感谢信,感谢帮助在港内地生的热心人士,也向港中大内地生收集学期结束后他们在学业方面的诉求,徐静怡觉得他们能做的也只是这些了。当内地生遭到舆论谴责的时候,联会没有办法替他们发声,因为“他们不能代表全部人的立场”。
平行时空
林峰仍留在香港。他每天早上前往学校,自习一天,晚上再回到合租的房子里。16日,示威者在学校设置了“关口”,但只针对警察——他们称作“狗”。所以林峰还是可以自由出入,也没人检查他的证件。
林峰觉得香港本地生和内地生完全生活在两个圈子里,“香港的大学应该都是这样”,除了一些课程有和本地同学组队完成作业的需要,他觉得可以四年不认识任何本地同学,大学照样能读下来。虽然在香港念书,林峰还是“把内地的那套生活动线搬了过来”,用微信聊天,上内地的网站。
“他们和我们的生活动线、信息来源完全不一样。”
秦乐博在他的宿舍有时要负责组织一些活动,因为楼层里内地生很多,他想建一个微信群方便联络。结果他收到了一个本地生的匿名抵制,说在香港他们不用微信,“不好意思,我们用Whatsapp”。
秦乐博常听本地同学用“香港大学平行时空”这个比喻,他感觉自己也是生活在另一个时空里的人。虽然他也用一些香港人常用的软件和同学交流,但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个看的还是微信。“增进情感要建立在交流的基础上”,即使身处同一空间,秦乐博还是感觉年轻一代的内地生和本地生被隔开了。
一堵墙好像真的把内地人和香港人分隔在了罗湖和新界的两岸。
今年国庆前,曾鸣的一个学妹发了一条朋友圈,想要在学校找个地方挂上国旗,问有没有人想和她一起。响应那条朋友圈的人不少,曾鸣也是其中一个,他们建了个群。那段时间,校园里有很多反党反政府的标语和海报,尤其是曾鸣听说在国庆当天,还会有针对党和政府的活动。他们觉得不能让这小部分的声音代表港中大所有的学生,“至少绝大部分的学生还是在正常生活,并且热爱祖国的”。
查阅国旗法后他们发现,如果国旗挂出去之后遭到毁坏或侮辱,他们是要负一定责任的,所以他们放弃学校标志性的地方,选择了比较稳妥的宿舍。
国庆当天,两面国旗在曾鸣和那位学妹的窗外挂了出来。学妹的宿舍遭到了威胁和攻击,不停地有人砸门,不明的水从门缝底下倾倒进来。学妹向学校的保安处和宿舍的管理员求助,尽可能地保护她的安全,但最后没有对攻击她宿舍的学生采取任何惩罚,“几乎是不了了之”。而曾鸣的宿舍没有遭遇什么状况。只是有网络暴力,三四百条的谩骂消息,他因此短暂卸掉了Facebook。
曾鸣能感觉到整个环境是在压抑和排斥他的,“特别是在网上浏览的时候”。受到网络暴力时,动不动就有人让他“滚回大陆”,“仿佛是两个隔绝的世界” 。
国庆的时候,很多在港内地生聚集在一起录制国歌快闪。在港大最大的广场中山广场,内地生们站在台阶上齐声唱红歌。秦乐博没有去参加,那时学校里可以看到一些对党的侮辱性标语,他可以感觉到内地同学很受伤,但他觉得国歌快闪比起政治意义更多的是“抱团取暖的身份认同感”。
对才进入港大几个月的秦乐博来说,他已察觉到内地生交到香港朋友是件很困难的事了。 国歌快闪之后,香港本地同学和他聊天,也会说他们很受伤,“他们说自己有种被占领的感觉”。秦乐博感到,在这个事件里“双方都放弃了沟通”。

林峰回顾他在香港生活的四年,从初次进入港大校园见到到处的标语和海报,他对本地生的态度从抵触转变为接纳、理解,最后又转变为“觉得不对”。最开始和本地同学聊天的过程中,会慢慢理解他们的想法。但过了一两年,他知道了“他们想要什么”“事情会怎么发展”之后,他走向了他们的对立面。
2017年,张翔接任港大的校长,一些本地生对他的意见很大。“他们会说,张翔是内地人,又在美国读的大学,他了解香港吗?”但林峰知道张翔最大的诉求是恢复港大的学术声誉和学术纯净。他觉得本地生的那些理由都是“粉饰”,“他们只是为了反对内地人而反对”。
林峰说,接受了内地18年的教育,价值观其实已经很稳定了,就是希望社会能够稳定,“大部分的内地生应该都是这样”。
今年9月的学期刚开始的时候,一个本地女生帮了徐静怡一个很大的忙,那时她正处在一个非常无助的时刻。为了感谢那个女生,徐静怡请她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便“不可避免地”聊起最近的生活。本地女生向徐静怡诉苦,说她已经半年没有回家了,因为她参加“反送中”的活动,家里不支持她。
那顿饭后,徐静怡再次感到,“真的不能跟香港本地人有太深的交流,深入交流就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政治观点的不同”。
在港内地生中,张欢乐属于本地朋友比较多的人,她说这也是“没有办法”,她的专业一届有一百三十人,而算上她只有3个内地生。
今年9月回浸大之前,因为“反送中”的事情,张欢乐有预想过可能会跟以前还聊得来的本地朋友们无法沟通。但开学后,她发现他们的交流完全没有改变,跟每个本地朋友交流都和之前一样。
在浸大的四年,刚开始和香港同学接触的时候张欢乐也会感到很沮丧。大一的时候她不会粤语,连听都听不懂,愿意和内地生多交流的只有父母某一方是内地人或父母在内地经商的同学。她感到,在香港,语言的差异是一个很根本的差异。但后来她想这样是不对的,虽然存在着差异,她觉得需要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做一些事情。
今年9月刚开学,张欢乐因为策展认识了一个本地女生,那个女生后来自己在校内策划了一个展览,展览的主题是“国王,士兵,花农,蜜蜂与青蛙”。这个展览用一个童话故事来回应“反送中”的事情,策展的同学每个人要换位到一个角色的位置上去布置一个作品。

展览开幕的时候张欢乐去了,观展中间,她和那个女生聊天,女生问她对整个事件是什么感受,女生说:“其实我真的不介意你是什么立场,只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说话。大家要聊这件事情才可以。”
张欢乐知道她说的有道理,但她也知道打破墙壁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
在进入港中大的一年多时间里,余滴认识了很多本地朋友。有一个本地同学总是会尝试在政治观点上说服她,她就在觉得同学说的不对的时候和她“吵架”。第二天,同学又继续说服她,同时她们也还是能正常地交流交往。本地朋友们也会和她开玩笑,会在她回到深圳后问她安全了吗。
余滴离开香港前的那个晚上,凌晨两点,一个本地朋友过来找她,因为她怕以后可能见不到余滴了。她问余滴会不会转学,担心余滴那晚没吃的,从给参与者分配的面包里拿来了两个给余滴。
她告诉余滴明天她要去参加活动,余滴问她去干嘛,她说:“去打麻将。”
“他们”
今年10月7日,秦乐博的一个朋友从广州来找他玩。朋友对示威的情况很好奇,那天在旺角有游行,他们就想混到记者的队伍里去观察,看看到底两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到底有没有暴力行为。
可是那天下了一场暴雨。他们在旺角迷路了,错过了真正的游行。但当他们拐进一条旺角到尖沙咀的主干道时,他们看到了游行后废弃的街垒,砸碎的玻璃,福建人开的优品360超市被砸了,一家中资银行在燃烧。他们路过被毁坏的旺角港铁站,站内的应急水龙头在往下喷水,淹掉了一半的港铁站,警报在响。
因为交通被堵,夜间大巴停了,秦乐博和朋友就在那附近晃荡了一个晚上。他们看到穿黑衣服的示威者们在餐厅里聚在一起吃饭,“像往常一样,感觉没有什么事情”。
学期初,秦乐博的一门通识课上,一个同学罢课了两周。那段时间罢课的声势浩荡,网上小组讨论时,那个同学告诉他们他在罢课,罢课两周。但是两周之后他就回来上课了,并且积极参与之后的课程。
同为港大大一内地生的邓紫在开学时看到港大地铁口的静坐活动,坐在两边的全是法律系的同学。她看到他们一边静坐,一边拿电脑在赶作业。
10月4日反蒙面法通过后,邓紫发现每节小班的讨论课上总会有两三个戴口罩的同学。他们只是无声地用行动抗议。在一门法律系的讨论课上,当他们讨论反蒙面法是否违宪时,戴口罩的同学发言也小心翼翼,“大家还是基于理性地讨论”。他们表达政治的行为和日常生活分离得很清晰。
每次在宿舍的公共厨房做饭,邓紫都很开心。做完饭后大家会坐在桌边一起分享、聊天,内地生、本地生,还有外国同学。邓紫参加了一个本地同学办的广东话班,她觉得课上的本地同学都很可爱。他们的普通话不好,但还是努力在普通话里找可以对应广东话的词。一次对话练习中,一个本地同学讲得特别快,他旁边的本地同学就笑他,让他讲慢一点,干嘛那么着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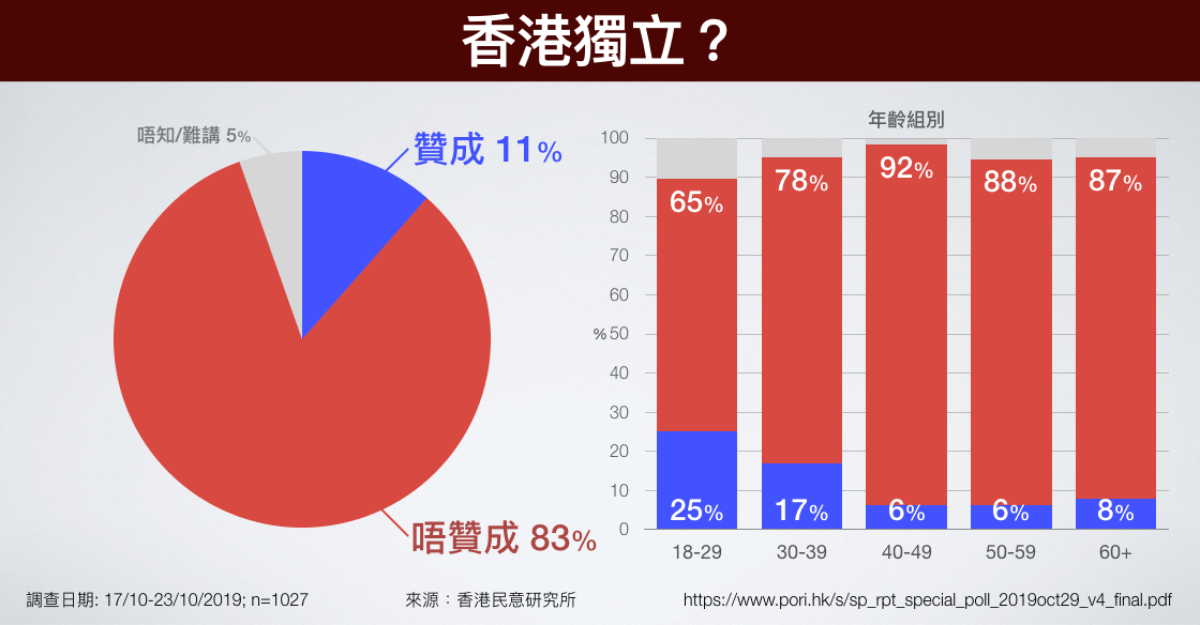
催泪弹的气味飘上七楼,黑衣示威者在楼下走。
这是徐静怡第一次接触到示威,也是“反送中”的示威活动刚刚开始的时候。今年暑假期间徐静怡在港岛实习,在附近租了房。她本来计划毕业后留在香港工作。
暑假期间,刘一城也留在香港实习,200万人大游行第一周的周末他路过了港岛。他之前有看到游行的消息,但他忘记了。他坐在巴士上想去港岛拍照,经过的一条路上几公里全是人,从铜锣湾一直延伸到政府大楼。他觉得当时的示威很和平,而且700万的香港人里200万人都站出来了,“表示一个很普遍的民意”。
还有一次他碰到了示威者在警察总部门口的抗议。那天,刘一城和一个韩国同事下班一起走,他工作的地方离政府大楼很近,他们远远地经过警察总部,很多人把警察总部围起来了,齐声用广东话喊着“放人”,抗议警察的暴力行为和抓人。
刘一城和韩国同事站在远处,韩国同事比较好奇,他们就停下来聊了几句。很多穿黑衣的示威者和他们一样站在远处,当时很热,旁边站着的示威者就给他们递湿纸巾让他们擦汗。
示威活动在港大校园里的影子,邓紫看到的就是无处不在的喷漆和海报,每到周末的时候被清除,过两天又再次出现;9月底10月初左右,在港大港铁站人流量较大的A口每天晚上都会有戴着防毒面具的黑衣人,他们在那里唱歌和宣传,教经过的人怎么跳过闸机,“他们称港铁为党铁,因为港铁会配合港府和警察”。
余滴每一两周就会去港中大附近的沙田逛超市。那边晚上会有人围在一起集会,中间有人在演讲。每周日会有同学在学校的百万大道“练武功”。
邓紫觉得反蒙面法的公布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在一个不适当的时间“火上浇油”,从那开始示威者们的行动开始超出了原来的“固定模式”。
10月4日那天晚上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甚至波及到了原来从来没有波及到的宿舍,邓紫的宿舍楼下,被认为是美心集团旗下的元气寿司、东海防水还有中国银行全都被砸毁。
那之后,邓紫对布满裂纹的防爆玻璃已经见怪不怪了,每天上学都会碰到。
曾鸣觉得港中大里的那些涂鸦和标语在这几个月里经历了三个变化阶段。本来只是一些“合理诉求的表达”;到9月下旬“怨恨”和“嘲讽”的话语慢慢多了起来,学校教学楼的墙上写着“血债血偿”四个大字;到了后期“卖惨”的标语越来越多,他会看到一些“不知真假”的遭到警方性侵或攻击的照片被贴出来。
余滴这学期去参加了一次枕头大战的情绪工作坊。组织者请大家把最近遇到的伤心事讲出来,在场的一些本地同学说自己身边的人被暴力伤害了。余滴看到他们哭得很惨。
余滴身边的一些本地同学周中在学校上课,周末就去市中心游行。他们还会去医院看望他们住院的朋友。
10月10日,港中大的校长段崇智在港中大的礼堂和学生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在谈话的几天前,段崇智的办公室遭到过一些学生的冲击。校长办公室门口被写上了黑色的标语,有人直接冲进了办公室,当着校长的面撒纸钱。曾鸣记得他们最主要的诉求是希望校长能够站住来保护他们,让警察释放他们的同学。
11月8日,四天前在一次示威集会中坠落的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梓乐不治身亡。当天,科大向全体职工和学生发送紧急邮件,称学校当天所有课程和官方活动取消、一些校园服务暂停,邮件的最后写着“take care and be safe”。那天晚上,余滴走回港中大宿舍,一路上都看到周同学的追悼会。
11月11日前的周末,余滴的一个本地朋友说:“大家不罢课,只能我们让你们罢课了。”她让余滴帮她交一门课程的作业,后来,那个作业余滴自己也没法写完了。
以香港九所大学为范围的大罢课开始了。示威者们把校园当作“根据地”,与外部的警察对峙。13日、14日多所大学陆续宣布学期结束,或是全部面授课程改成网课。
那天之后,每天仍出入港大校园中的林峰发现示威者对他“完全不care”,之后立起的“关口”只是针对警察的。一天晚上,示威者还在学校里开了一次座谈会,向来听的人传递信息,试图展示他们这个群体的全貌。
当曾鸣去看示威学生跟段校长和跟警察的谈判时,他觉得他们的诉求其实“很简单”,简单到让他觉得“很傻”。他们跟校长提出的是让校长“保护他们”,甚至不需要校长站出来公开支持双普选。他们跟警方提出的诉求是“把我们的同学放了”“不要因为我今天扔东西怪我”。曾鸣觉得,他们一边做着这些的时候,一边心里又感到无比害怕。
而他们这种“团结的精神”又让秦乐博感到害怕。示威者以“手足”相称,他们之间有着“不割席”的原则,即只要站在示威者一边,不管是“和理非”还是“勇武派”都不互相指责。
秦乐博觉得他们好像被一种火热的气氛给点燃了,他理解他们因为诉求得不到政府回应而行动升级,但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好像觉得攻击警察家属也是可以的,他觉得“挺吓人的”。
11日以后的一周,示威者对学校的破坏让邓紫感到非常心痛和难过。当她像“逃难”一样离开香港的时候,示威者在学校里吃着方便面。她完全不知道现在的他们要干什么,“为什么他们守护城市要以破坏城市为基础”。
回到深圳后,余滴问她的一个本地朋友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我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本地朋友告诉她,她也觉得没有办法了,但只能坚持下去,“坚持下去才会有结果”。
还有在这种集体氛围之外的香港本地生。
曾鸣说,据他的了解,黑衣“暴徒”在学校里只是极少数的群体。他知道身边的一些本地同学是支持“反送中”的,但他们只会用比较“温和”的方法,比如在反蒙面法通过的时候,他们会戴上自己的黑口罩。还有对示威比较反感的同学,每次一有活动的预告,他们就会早早回家,不在学校里逗留。“所以他们发声比较少,而暴徒发声比较多。”
一次,邓紫参加高桌晚宴,晚宴结束后突然有人带头唱起了《愿荣光归香港》,渐渐整个厅都回荡着这首歌。邓紫发现坐在她对面的学姐没有唱,这个学姐之前主动用普通话和她交流,还分享给她很多课程资料。可是,当唱歌结束大家喊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时,那个学姐却一起喊了起来。邓紫感到很困惑。
秦乐博的一个本地同学告诉他,他们一些人其实并不怎么参与整场运动,但是当周围的人开始抵制美心集团的时候,他们也只能迫于同辈压力而不去吃美心。
一个法律系辅修公共行政管理的本地同学和秦乐博聊过很多次天,跟秦乐博聊他觉得为什么香港的年轻人会感到绝望:香港近些年爆出越来越多的社会丑闻,比如他们本来以引为傲的廉政公署的丑闻,对于香港人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他们觉得造成这些的重要原因是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被操纵了,变得不再民主、自由,其下属职能部门的选人标准不再是一个人的能力而是他的政治立场,导致了行政人员的能力低下和腐化。最终,他们将社会的所有衰落归因于没有实施“双普选”。
邓紫刚入学的时候,收到了法学院院长的邮件,院长邀请所有的内地生一起吃饭。吃饭的时候,院长和内地生们聊天,问他们刚到香港来的感觉怎么样。邓紫觉得“特别温暖”。
当示威者占领了学校之后,邓紫在一段视频中又看到了他。视频里,头发花白的法学院院长站在停运的港铁站里,面对十几个黑衣人,用英文说:“暴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你们是香港大学的学生,你们可以做得更好,你们必须做得更好。”
港大的校长张翔也经历过被包围。因为张翔很久不在示威活动中出现,示威学生们指责他不出声,“胆小鬼”。11月1日,他们知道张翔要参加一个中午12点的会议,早上他们就包围了开会的那栋楼,把这个活动叫作“用爱包围,盼爱回应”。
那天上午11点,港大的所有学生收到了张翔校长发来的邮件,邮件里写着:
“香港大学是自由和知识的堡垒,我们坚持理性的辩论和探索,致力以知识,智慧及想象,开创新天。我有责任维系一个活泼的校园,捍卫多元价值,互相尊重,让同学能在一个开放和安全的环境下学习和建构学问。我爱惜每一位同学,也关怀每一位同学,这也是我的责任。……我希望和同学们的对谈,重点不在我的公众形象,而是真正的坦诚交流,让我们了解彼此和香港的痛点。过去几个月来,我和同事朋友一直在思量如何破解困局,包括怎样在真诚、信任、尊重的基础上,理解大家心底的创伤。我期望在本月内举行一场师生论坛,一起探索前路。”
“最重要的”
在秦乐博的妈妈叫他从香港回家的时候,他和他妈妈在电话里吵了一架。
“大家知道香港到底在发生什么吗?真相是什么?他们的诉求是什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
电话那头,他妈妈对他说:“这些事情一点都不重要,对我来说,重要的就是你的安全。”
秦乐博不说话了。他知道他妈妈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他知道自己不能让她感到难过,不能让重要的人感到难过。
回到家之后,秦乐博倒头大睡了好几天。他觉得自己真的太疲惫,张口闭口和很多人说了太多关于香港的事,很多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太痛苦。原来他觉得社会公义之类的东西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事,但当他在香港经历了这些,当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正义的时候,他开始不清楚怎么样才是对的。如今他觉得做一个“很普通的人”好像也是可以的,就像《阿姆斯特丹夜机》的一句歌词:“我已經有愛人/香港冇我嘅事”。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都有自己过去的经历,有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当要把这么多言语全都集合起来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弥合这些矛盾。你不能让示威者不再流血,你不能让香港市民不再因为这个事情而受伤,你不能在一夜之间让大家安居乐业,没有人再感到痛苦了。”
秦乐博现在在考虑转专业的事,并且先把精力放在学习理科和喜欢的乐器上。他把这看作是一个重新探索自己的机会。
离开香港后,徐静怡和其他离开的内地生聊天,大家在港中大宣布学期结束后一起讨论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还要不要写作业,之后还会不会有考试,另一个是会不会退不退学费。
秋招中,徐静怡申请的全部都是香港的工作,如果放弃这些申请,她想她可能要gap一年。所以她决定在深圳先住下来,等待之后的情况。
林峰的四个内地室友都和林峰一样选择了留在香港。林峰说,他们留下来的原因都很“现实”。有人担心拿不到毕业证,有人因为正在写的论文必须要用港大图书馆里的文献,有人正在做兼职实习不能离开,有人因为回家的机票太贵了想等到过年的时候再回去。
“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黑衣人也是。”林峰说,“或者说他们自以为的利益。”
邓紫本来就计划好11月11日后的那周要到深圳玩。在深圳呆的几天,她每天换一个酒店,走到哪住哪。港大宣布学期结束后,她妈妈就给她买了周日直接回家的机票。回家前一天,她看到香港市民自发清除路障的视频,视频里市民们排成很长的几列,从前往后一块块传递砖块。看到这些,她又不想回家了,好像感觉过几天一切都会好起來。
余滴也说起市民清除路障的事,她觉得好像看到了一点方向:“可能就会这样没了。大家都想好好地生活。”
感谢11位分别来自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的受访者。
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
文中图片和视频截图皆由受访者提供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