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风流当借口,性骚扰就是性骚扰
出版人范新、作家宗城、编剧史航,以及南京先锋书店某员工等多位文艺界人士,均被指控有性骚扰行为。
文化人历来是“社会的良心”,开口秦皇汉武,闭口琴棋书画。但文化人也不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当然也有一些真有良心的。
几位文化人是否符合《民法典》中“性骚扰”的条款,有待确证,我们不必急于辩解谁有罪、谁无辜。
而控诉之外,女性普遍、隐秘的苦痛和代价巨大的反抗,既暗示了公道和实力的性别分割,暴露了文化资本的无形“魅力”,也揭示了女性文化革命的持续缺席。
文化人的糊涂账
文化人的性骚扰,像一笔“糊涂账”。特别是其他文化人辨析“性骚扰”,颇有“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之风。
近来的糊涂账大概分为三笔。
有人说,骚扰时没有当场打回去,就是“同谋与帮凶”。既然当时选择“屈从权力”,那么后来的“质疑与声讨都是可疑的自我指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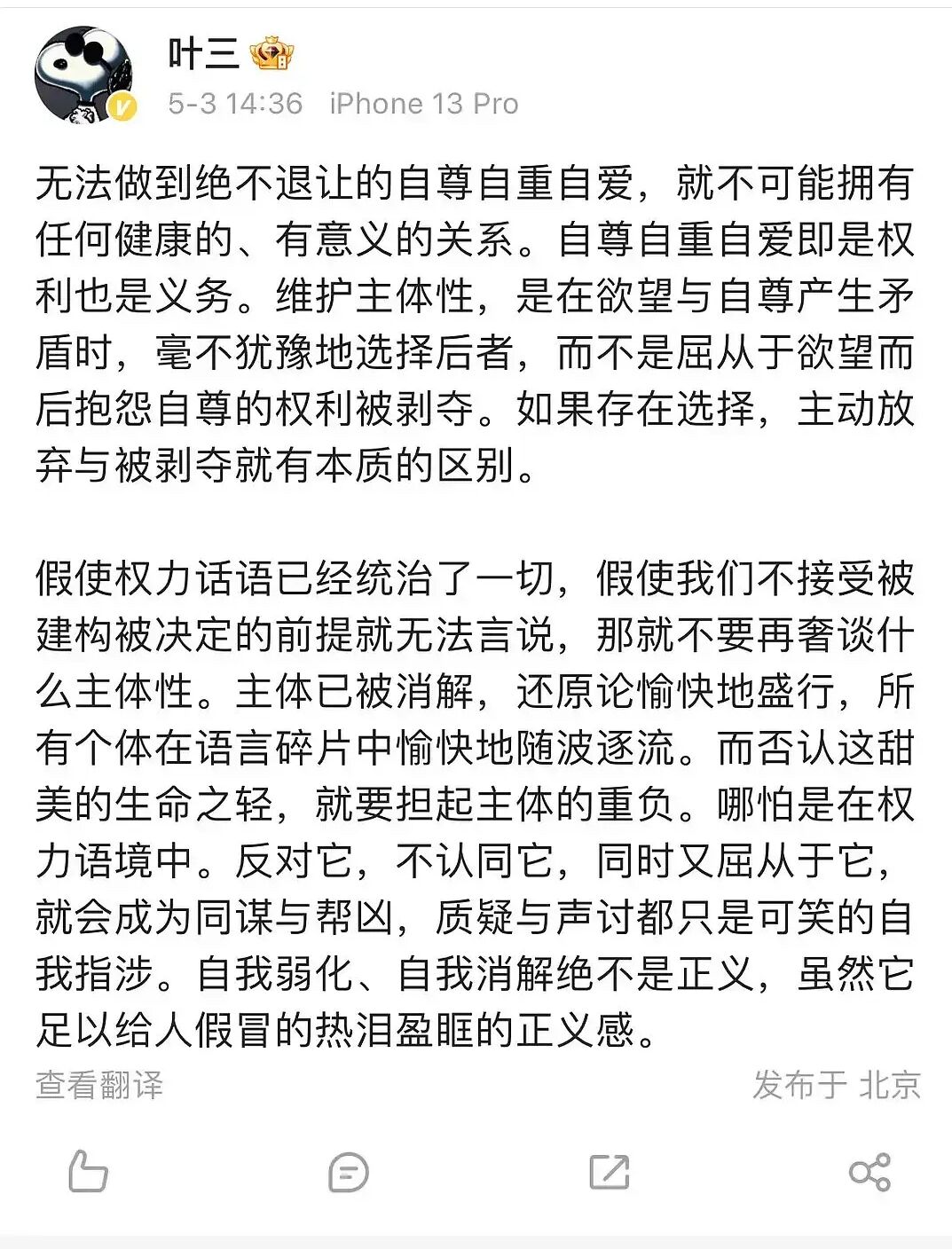
虽然使用了大量“主体性”等学术黑话,但这位文化人的意思无非是,“事后诸葛亮”在道德上很不纯粹,没什么资格指控性骚扰者。没有“狠斗私字一闪念”,就跟坏分子属于一伙的。
照这样的意思,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在电光石火的时刻是不允许有任何困惑的——不仅要时刻保持内心清明,还须有“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硬功夫。
还有人说,文化人性骚扰是几千年性压抑的结果。这种“深度”剖析可能是专栏作家的通病——跟做托福阅读理解常见错误一样,“推得过远”。每个热点都要发声,每个热点都需要挖掘根深蒂固的制度性问题,性骚扰只好跟性压抑挂钩了。其实还可以再加上“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毕竟八十年代这一类理论的批判范围“无所不包”,针对传统文化的“沉疴痼疾”都比较好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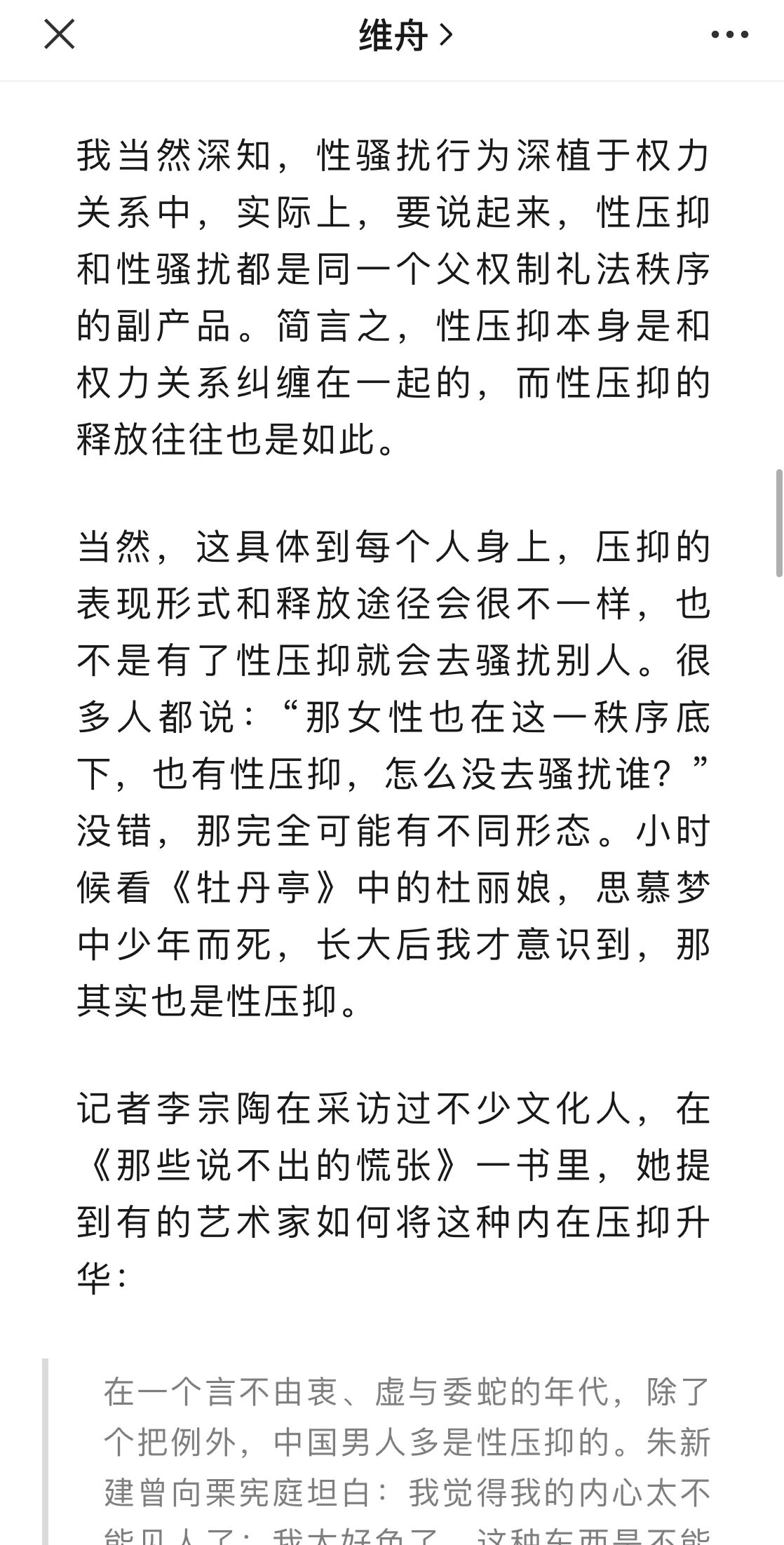
性压抑的说法属于捣糨糊。如果性压抑就要导致性骚扰,那么全世界的人都缺钱,怎么不见大家都“偷偷摸摸”抢银行?还不是因为看守钱的人手里有“真家伙”。要是把捏软柿子的坏人都说成文化心理的“受害者”,死刑的“合法性”都得存疑。
也有人说,性骚扰存在“情境问题”。作者引用了学者玛丽·比尔德《女性与权力》后记中补充的一段,1978年,比尔德曾于火车卧铺上与一位刚认识不久的男子发生性关系,2000年她叙述此事时认为“或是我有意识做出的选择……我抱怨说自己在米兰被一个男人‘泡到’(pick up)”,而2018年“MeToo”运动时,她将这段经历定义为“自己被强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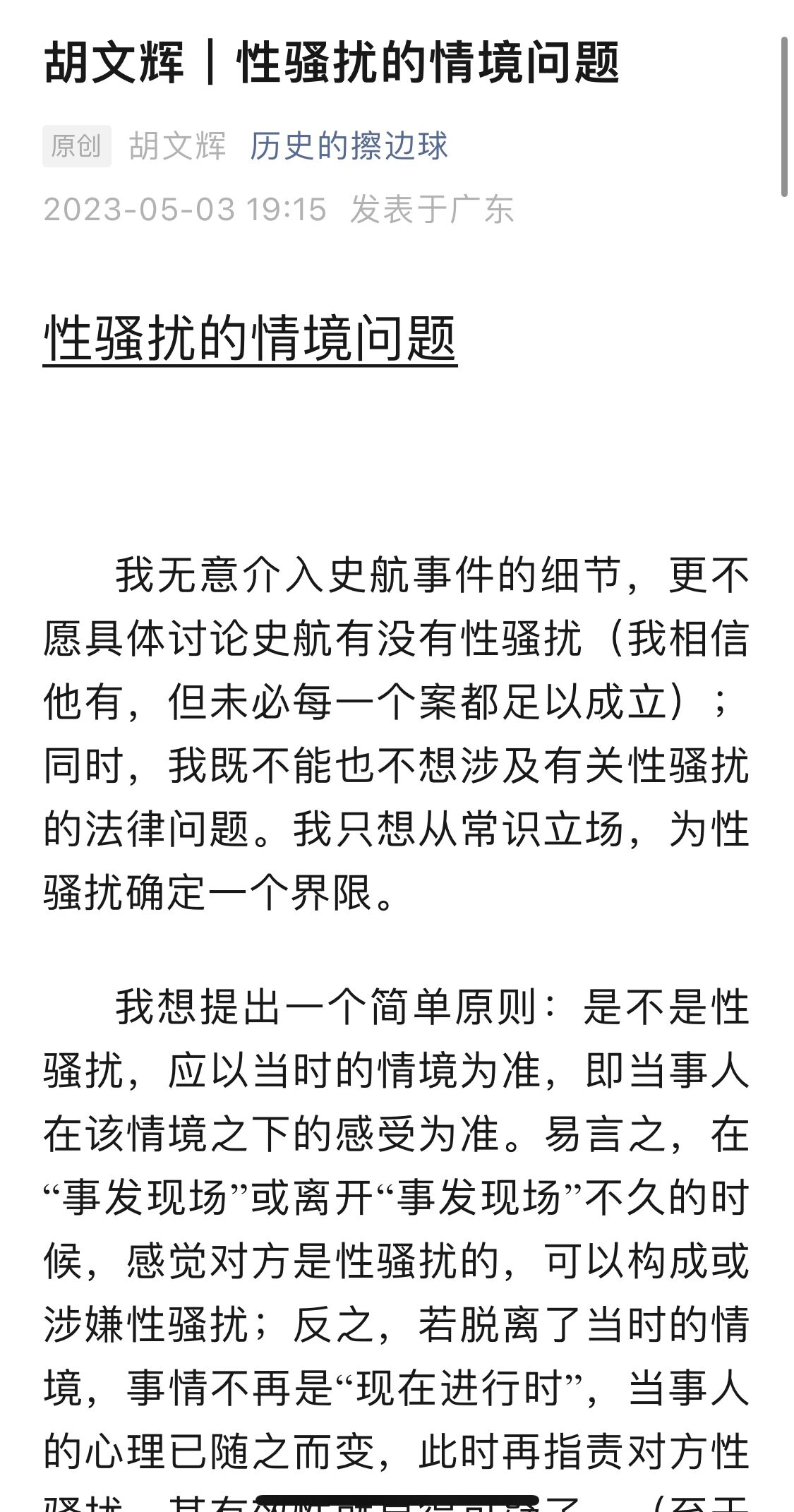
作者强调,玛丽·比尔德的自述文本前后存在巨大差别,证明个人心理和判断随着情境不同会有较大变化。如果脱离情境,对性骚扰做事后追诉,存在法律上的危险。
这一提法是必要的,但也并非绝对。2017年多位美国女性控诉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性骚扰时,很多事件发生在数十年前,寻找证据非常艰难。律师、封口费、电话记录……总有细微的证据留下,将犯罪者最终推向审判席,还无罪者清白。
一旦以“情境问题”等条件来“压制”诸多受害者的发声,或者令大多数沉默的受害者心生恐惧,那才是犯罪者的“帮凶”。
即使由于证据不足,被控诉者没有被“绳之以法”,控诉者“黑尾鸥1988”也已经清醒地呼吁:“性骚扰,自始至终,不是性欲的问题,而是权力的问题”“我们不要他禁足一礼拜,我们要他偿还我们被摧毁的人生”“核心诉求不是法律制裁,而是揭穿他的嘴脸,让公论留在正义之士的心里”。
而作者忧心忡忡“反性骚扰不应该成为一个针对男性的道学运动,不需要给男性戴一条道德和礼教的头巾”,总有点率先“跳反”的意思。事情还没完全揭露,甚至很多女性尚没有发声的机会,有些文化人已经急了——你们搞运动不要扩大化,我们大多数男性可是好的。
三笔文化人的糊涂账,一言以蔽之:女性控诉者必须全知全能,心平气和,智识高超,步步为营,进退有据,稳健圆满——最好永远在研究室里研究自己“被性骚扰”的所有条款,体谅大多数男性的“不容易”,并且永远还差一个精确的证据。
文化人的迷惑性
想进步的文艺青年,往往喜欢寻找一位精神导师。如果导师是死的,还稳妥一点;一旦导师活着,同时好为人师,多半有点危险。
鲁迅就说,寻找导师的,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因为凡是自以为“老马识途”的,顶多是年纪大一点,圆滑稳重一点,自己误以为自己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早就朝目标进发,何至于还在做导师。
佛教也有类似的说法,有人自称菩萨、阿罗汉的,九成不可信。只有一种可信——说完自己死了。《楞严经》中,佛说“我灭度后,敕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形,度诸轮转……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泄佛密因,轻言末学;唯除命终,阴有遗付。云何是人惑乱众生,成大妄语?”
导师也不好一概抹杀,总之不要有太高的期待。会说话的,不过就是舌灿莲花;会弄笔的,无非是文采风流。假如大家又希望他能搞人工智能,就是自己错了。他如果能搞人工智能,早就去搞了,而那时粉丝还希望他会刻芯片。
导师靠不住,五四以来的青年很多都“觉悟”了。
王朔小说《一点正经没有》里,有位自诩导师的赵尧舜,故事最可笑。

他要么劝“顽主”看书,因为“书是消除烦恼解除寂寞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啊”,被后者怼“我们没什么烦恼。从来不看书也就不烦恼了”。他要么不赞成管年轻人叫“垮掉的一代”,因为有追求的年轻人才能引领人类“不断前进”,“顽主”不客气地说"看来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对人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名字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赵尧舜,最后还是折在了“男女关系”上。“顽主”骗他有姑娘想向他学习请教,害得赵尧舜巴巴地在街角干等了一天。

然而自己也靠不住,很多人还未意识到。
民国时期,《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有一位青年大发牢骚:“只有自己可靠”!
鲁迅还想“斗胆转一句,虽然有些杀风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因为“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我们还没有正在饿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饭,正在穷得要死时与无人处见别人的钱,正在性欲旺盛时遇见异性,而且很美的。”
“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
半边天的困惑
1949以来,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有强烈的外力推动色彩。妇女的权利得到法律形式上的确认与保护,通过社会主义实践,女性正式拥有“半边天”的地位。

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运动,一直缺乏内在的文化革新。直到今天,女性依然很难脱离秦香莲和花木兰的“二元境况”:要么和前者一样,是父权和夫权损害的弱者;要么和后者一样,是和男人几乎没有差别的女英雄,并且只出现在男权式微之处。
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者”,比如前一阵子和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对谈的“全嘻嘻”,一边给自己冠以夫姓、用生孩子“拴住丈夫”;一边自称“女性主义者”。

彩礼女权两不误的“女性主义者”的存在,恰恰暴露了中国女性内在的、自生的“权利”观念的缺乏。
一方面,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当代女性已经对“妇女解放”话语感到极度的疲惫和隔膜;一方面,大众传媒、社会生活中常见的歧视和不公,往往得到规则的默许——女性必须要跟男性分享相同的自我想象和自我定位,做抹杀性别差异的花木兰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这种割裂导致女性对精神性别的思考和实践,充满了无知、困惑和矛盾。
同时“男女都一样”的话语,实际是一种“双重标准”,为女性带来了双重的负担:女人既要和男人一样,作为社会的“主体”来服务社会;也要“不言而喻”地照顾家庭,为生育子女付出高昂的身体代价,为整个家庭付出难以计量的情感劳动。
电视剧《狂飙》里,令观众津津乐道的“大嫂”,实际是“大哥”的影子。电影《爱情神话》里,三位女性围着一位中年男人“老白”——一个拥有上海“独栋”的离异落魄男人,在婚恋市场上甚至可以“选妃”。导演说:“我无法用女性视角去叙事,否则那将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在流行文化里,观念的更迭是缓慢的,但确实是在推进的。
二十多年前,流行女歌手蔡依林的歌曲《爱情三十六计》,放在今天肯定会被批评“媚男”。
如果一位男性在感情中不能提供情绪价值,热心的豆瓣网友都会劝女生“分手”——很多女性敏锐地发现,男性缺乏情绪价值,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他们对处于权力上位的领导,从来不会“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这些评判未必是公正、客观的,但已经体现了新时代女性从新的角度思考性别问题的倾向和努力。
哈维·韦恩斯坦的事情披露后,“MeToo”运动大爆发,新的争论不断浮出水面。今天,针对数位文艺界人士的“性骚扰”指控,应该得到舆论的进一步公开。当受伤害的女性鼓起勇气说出故事,不会被强行打压,不会被秋后算账,那么不公平的现象就有希望得到纠正,哪怕其中存在着虚假的述说。
新的争论、新的分歧,正是重新塑造和改革性别文化的最好契机,也将促使女性真正从“内在”反思自己的精神定位。
当然,我们同时必须思考:大规模指控的目标是要杜绝性骚扰,改革民事司法体系,打碎父权制,还是要提倡无冒犯的调情?这些指控和究责,是否会导致无限上纲上线,令无辜的男性动辄得咎,还是说运动尚且推进得不够,根本不足以撼动旧的不公平的现实?
纵有知音见赏,不辞遍唱阳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