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漏れ日日和——《新活日常》的木、日、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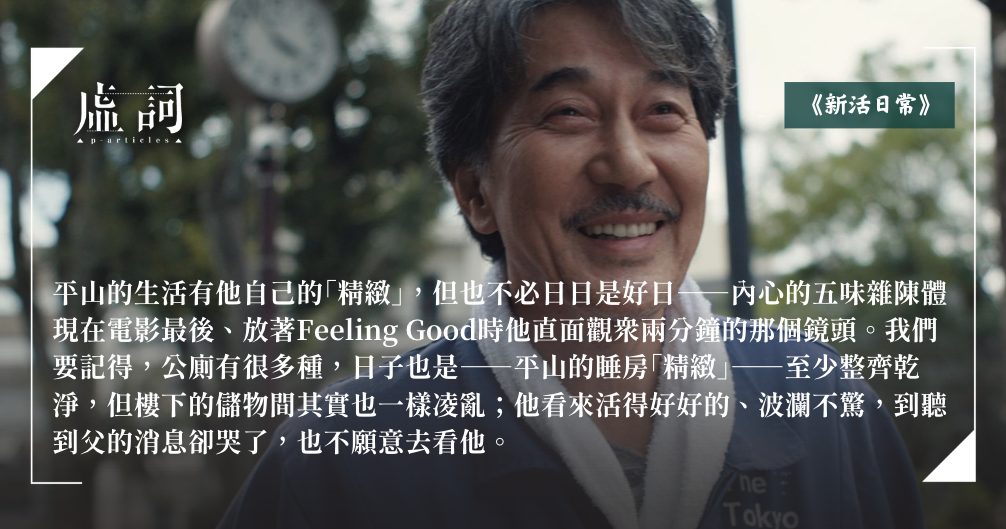
文|雙雙
看完《新活日常》(Perfecct Days, 2023)的那晚,想到中學圖書館西北隅的小木櫃。
1. 木:中學圖書館西北隅的小木櫃
小木櫃有多得出奇的小抽屜,像暗沉的褐色紅磚在品地壘成牆前,田的方整地疊放在那裡。靠近去看,木的紋理流麗如浪。記憶中,在休館時分,當圖書館關上所有電燈,而冬天易晚的夕陽透過新古典主義的窗,像軟鐘一樣攤開在自修區平白的塑料長桌上時,小木櫃就在最北的窗再北、西斜的光照不到的角落,彷彿陰影是幅被子,小木櫃把它拉過來蓋起了自己。
那是個存放卡片目錄(card catalog)的小木櫃。

據說,這個圖書館大概在平山(役所広司[1956-]飾)出生的年代就在這裡了。我想,也不至於遠在那時,小木櫃就已經在這裡,不過,也該是月島雫(耳おすませば/心之谷,1995)、渡辺博子(Love Letter/情書,1995)她們的那種年代上下——在還沒有電子書和電腦借還書系統前,人們借書,要在夾在書內的借閱卡留名,月島雫—天沢聖司、渡辺博子—藤井樹之間就是靠借閱卡連起來的了;在電腦圖書檢索目錄前,人們找圖書,就是用卡片目錄。
卡片目錄就是一個櫃有很多抽屜,抽屜裡放著一大沓卡片,卡片按字母/筆劃序排好。每張卡片都是一份微縮的表格,標記著書名、作者……和最重要的索書號(call number)——按字母/筆劃在抽屜找到指定的目錄卡片,按著索書號,就能在書架上對應的位置找到要找的書。
每張卡片都大同小異——畢竟這是表格/形式的暗示:統一、規範,只保留最少限度的變項、無可避免的差異。它們擁有各種缺點——數量繁多,佔位置,泛黃,內容用原子筆手寫而不是打印,如今也完全沒有更新或用處。不過,即使當時,如果問我圖書館裡最「精緻」之物是哪件,我也會說是存放卡片目錄的小木櫃,並且指向圖書館的西北隅——畢竟卡片目錄跟借閱卡和磁碟(floppy disk)一樣,成了宜在提及時加以解釋之物。
那麼說,這種所謂的「精緻」,至少包含著四種意思——古雅、複沓、簡約、陰翳。
平山的生活日常像存放卡片目錄的小木櫃。他居住的小屋並不窗明几亮,也半點不新,但格調不失精簡(至少主要活動範圍是這樣);讀的是一本本、一頁頁的書,燒水用火(而不是電),用大概至多只能玩貪食蛇的手機、菲林相機,聽卡式錄音帶(cassette tape),不知道Spotify「在哪裡」。他的生活日常像卡片目錄——一沓重複的表格,統一,泛黃,手寫,沒有更新——但有一種極簡主義的質感。
目錄卡片像木漏れ日,乍看起來張張相似,但每一張的內容都 “only exists once”——平山拉開壁櫥,裡面是一個個銀色鐵盒,田的方整地疊放在那裡,標記著年月,裡面全部都是每天拍下的木漏れ日相片。
那就是他的生活日常的卡片目錄。
2. 日:木漏れ日的構成
木漏れ日之所以好看,之所以浪漫與詩,首先是因為那個木本來就不錯看——不是心無罣礙的枯松,也不是滴水不漏的龍血樹——要微風能吹動枝節杪梢,葉也足夠靈活,能讓陽光千變萬化;陽光最好別太狠毒,灑落一種和光同塵的明度,溫度也恰是秋涼上下,木漏れ日才會能看、才美。
美學往往是舒適的——即使是暴力美學也同樣,遭受暴力的不是我們,我們很舒適,就只是看著,沒多難受的。
當平山的第二天開始時,我思忖這會不會是一部波瀾不驚的電影——不驚得完全日常、如紀錄、如Joris Ivens的《橋》(De Brug, 1924)或者《雨》(Regen, 1929)這樣的片子,要在電影院看一百二十分鐘想必不是甚麼舒適的事——而平山恰好就是很橋和雨的人。
之前讀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秋山図〉(1920),說煙客先生去看黃公望(元代畫家)的隱世傑作秋山圖——第一次去看的時候在一間寒舍,秋山圖美得驚天泣鬼,十多年後在豪宅中重遇,竟覺得它等而下之。
也許不是畫本身的問題,而是環境之故。
「沉默寡言的東京公廁清潔工人平山,過著看似單調重複的生活」,電影簡介這樣寫。這樣寫首先讓我想到房慧真〈聊齋〉(《草莓與灰燼》,麥田,2022)說,廁所的「盥洗台不常是濕淋淋地,打掃阿姨時不時來擦乾水漬,補擦手紙,清空垃圾桶,噴上空氣清淨劑,保證一切無臭無味,乾淨順暢」,她「打掃阿姨綁著護腰,每天她要彎下腰清一層樓近百個垃圾桶。」以為平山會是「打掃阿姨」那種狀態,結果原來是The Tokyo Toilet設計精美的公廁,每一間都比我面前這個藍色海響瓶子還好看——這種背景襯托了平山的生活、舒適了畫面。
畫面之外就是情節,情節能撐一百二十分鐘,來源於他生活/命中的其它人物——他這人I得近乎絕緣,T同學就說這是她看的電影裡最少對白的一部。就比《悲情城市》(1989)裡的梁朝偉(飾林文清)多一些。還好,隆(タカシ,柄本時生飾)、綾(アヤ,アオイヤマダ飾)、丹子(ニコ,中野有紗),都是些動作和話都滿多的人,還有那位從沒出鏡的角色——平山井字遊戲的相手,把自己最後一個圈圈畫成笑臉。
井字遊戲有三種結局,贏、輸、和,前兩者想是比較少發生的(吧),因為井字遊戲的變化非常有限,只要雙方都稍諳井字遊戲的規律,就只能和了——電影裡也是這樣:對方第一步下在中間,平山下在角,只要不出意外,就是打和,沒有懸念。生活一樣。但是,不論是哪一方,當然都不必取勝也不求敗——就是「只求打個和」,過程中的快樂才是重要的事。生活一樣。
不是說沒有The Tokyo Toilet雲溫達斯(Wim Wenders)就不能拍出好看的畫面,也不是說沒有那些有趣的人們平山就不可能過有趣的生活——不過生命中總有些日子是「木漏れ日日和」(適合看木漏れ日的好天氣),有些不是。正如,平山的生活有他自己的「精緻」,但也不必日日是好日——內心的五味雜陳體現在電影最後、放著Feeling Good時他直面觀眾兩分鐘的那個鏡頭。我們要記得,公廁有很多種,日子也是——平山的睡房「精緻」——至少整齊乾淨,但樓下的儲物間(當丹子睡了他的睡房時,他睡的那個小房間)其實也一樣凌亂;他看來活得好好的、波瀾不驚,到聽到父的消息卻哭了,也不願意去看他。
有妙趣也有我去、陽光與陰影、小確幸與崩潰、笑與淚,交織混和,才是真切的生活日常。
3. 影:如果影子真的會疊加
甚麼東西最公平?陽光普照?睡床?死亡?影子最公平。一個小孩子(只要靠近光源)的影不必比歌利亞的小,乞丐的影子也不會比王子的淡薄輕盈。當然只是在物理學這樣。不喜歡物理學喜歡故事。不是有很多故事——尤其是兒童故事——主角的危機都是影子要離開或者變淡嗎?
〈聊齋〉裡的辦公室,「茶水間一三五有水果,二四給點心,還有一台義式咖啡機幫忙省下每日鴉片錢」,「廁所的擦手紙總填得飽滿,予人用之不竭的富足感」。人想必不會餓肚子,肚子隨時充實但卻有另類的空虛——「辦公室裡,他者皆幽靈,你穿過他們透明的身體,他們也穿過你如無物。」
「他們」的影子想必是很輕的吧。
泡完湯之後,丹子在冷藏庫拿飲料,平山說——餓了嗎?餓了去吃午飯吧,丹子欣然同定,就把飲料放了回去。
她/他們的欲望恰如其份。《涅槃經》說「少欲者不求不取,知足者得少不悔恨」(註1),丹子求也取了,但聽到有午飯吃就開心地把飲料放了回去,「得少不悔恨」,就是所說的「知足」了吧。
常言知足常樂,常樂不是恆樂,但要是恆樂那多沒意思呢,對不樂甘之如飴,就是所謂的「生活」——c'est la vie,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據說這句法語有這樣的意思)如此。
——默劇的關鍵在於,不是要知、道、這裡沒有橘子,而是,忘、記、這裡沒有橘子,而且,自己很、想、吃橘子,《燒失樂園》(버닝,2018)裡的海美(全鐘瑞飾)這樣說;她還說,有所謂 “Little Hunger” 和 "Great Hunger",前者是生理飢渴,後者對生命意義如飢似渴。她沒有橘子,就「默劇地」吃橘子;她虛無空寂,而追求某些遠方,就像貝蒂(37°2 le matin, 1986),最終「飢来驅我去,不知竟何之」。
彷彿她從來就不是一個生活的人、或者說不是生活在「生活」裡的人。
(順帶一提《燒失樂園》是很了不起的電影喔,它也是我所知道的電影中少數拍做愛時會有戴套這個環節的電影。)
從電影院出來,我們走在子時的街燈之下,L同學說,所以影子是真會疊加不?我說衣服有影子,帽子、口罩有影子,人也有影子,影子不分辨一絲不掛或衣冠楚楚啊。
我就想到海美,她在抽了大麻之後,在夕陽之下脫光了衣服,起舞——如果影子真的會疊加,那時,她的影子肯定很輕,很輕。
註釋:
從另一篇《新活日常》影評借來的。鄧皓天:〈Chill得其樂:身所處為虛,心所嚮為實——《新活日常》中的侘寂之美〉,虛詞,https://p-articles.com/critics/4339.html。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