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漠的雪櫃(靈異 / 笑話改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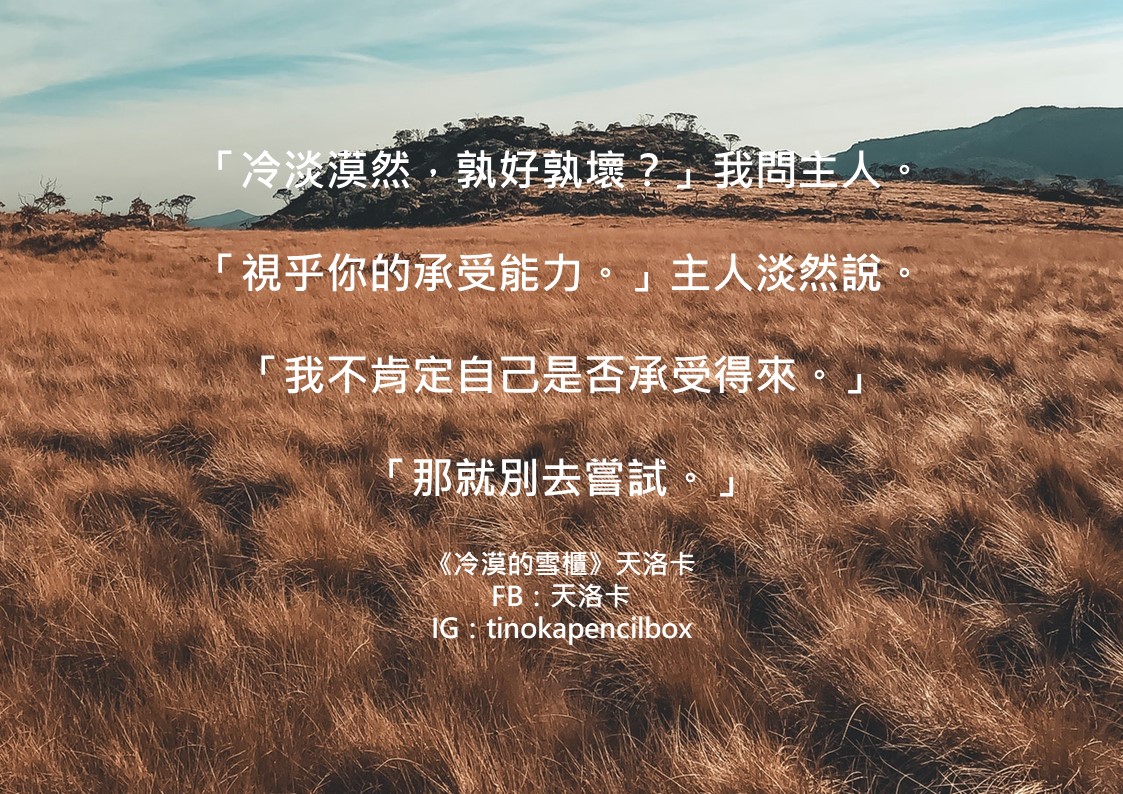
我是一座雪櫃,天生性格冷漠,有意無意冷待每個來者。嗯……這種說法不準確,對我不甚公平:每個被放置入我體內的來者本來就不需要熱情招待。它們要不垂死,要不已死。
某天,主人往我身塞入一頭巨型活物。這是我首次看見主人以外、生命力旺盛的活物。我霎時沒能釐清眼前到底是甚麼狀況,本能地順應天性,乖乖張開肚皮,配合主人行動。
活物拼命掙扎,奈何最終敵不過強大的主人。牠在我體內悲泣不止,我聽而不聞,默不作聲。
一星期過去,主人仍沒有放走活物。我感到奇怪:主人從未試過冷藏任何物體超過一星期。這活物到底有何特別?
我偷偷仔細觀察牠——修長四腿,頭頂兩角,大眼長睫,短毛遍體,最奪目的莫過於那不合比例的長頸。
「有話直言。別偷瞄偷瞥,這令我感到被冒犯。」
「你是誰?」
「長頸鹿。」
「甚麼?」
「長——頸——鹿——」
她的不善語氣充份表達出不耐煩。
我沒再多話,無謂自討苦吃。
***
沉默維持多日,首先耐不住死寂的是長頸鹿:「你還未告訴我你的名字。」
「雪櫃。」
「我知道你是雪櫃,所以我問的是你的『名字』。」
我深思數秒,恥感莫名生起:「我的機身編號貼在背板上。你有本事就自己往外頭看吧!」
「你明知我沒能逃脫!」長頸鹿生氣咆哮。
「別講成是我主動囚禁你——我也是被迫的!我恨不得馬上趕走你!你知道你把我撐得多痛嗎?」我按捺不住,將連日不愉快情緒發洩出來。
長頸鹿沒馬上回嘴。我以為牠在生悶氣,誰料牠竟報以淒涼啜泣聲。我不知所措:沒有遇過這種情況、這種外剛內柔的活物。
又是一陣熬人的寂靜。
事實上,我並沒有閒著,不斷在腦海反覆排練如何展開對話而不令長頸鹿感到難過。但無論我內心如何躁動,在長頸鹿眼中我仍是沉默如常,牠仍是率先打開話題的一個。
「抱歉撐痛了你。」
「毋須抱歉——你根本無法選擇。」
「如可選擇,我會回到我的故鄉去。那是一片廣闊的草原,有和藹可親的同伴、好吃的新鮮樹葉、熾熱耀眼的陽光和帶有草原氣息的涼風。」
「我知道甚麼是『同伴』、『樹葉』、『陽光』、『涼風』,但我想像不到這些東西湊合在一起會是何樣光景。」
「美好的,幸福的,快樂的。」
「我希望自己有幸能夠親身體驗。」
「如可離開這鬼地方,我定會帶你去草原。」
「噢!謝謝你!」
長頸鹿告訴我很多關於草原的事情,聽得我如癡如醉。惟牠問及我的故鄉時,我卻支吾帶過:冷冰冰的工廠,不值一哂。
***
我著實不理解自己的心態:明明長頸鹿把我撐痛,四個蹄印深陷我身內壁,但我偏偏習慣了牠的存在。
我討厭這種感覺——我彷彿不再完整,不得不依附牠這外物。
我故意減少與長頸鹿的交流。牠很快就察覺異樣,問是否牠說錯話惹我生氣。看牠眼水汪汪,我不忍撒謊推卸責任,坦言對牠存有心理依賴。
「那的確不是好事情。」長頸鹿幽幽回應。
沉默再次維持好一段日子,久遠得我開始懷疑自己不曾與長頸鹿交談過:那些快樂心動時刻不過我的妄想。迷惘之時,一道光打破我的思緒——廚房燈亮起,主人來了。他哼著輕快童謠往我走來,打開我的肚皮,手勢純熟拉著長頸鹿的腿往外抽拉。
長頸鹿拼命掙扎,如牠剛來之時。奈何牠被雪藏多日,加上未曾進食和補充水份,體力明顯遠遜從前。不消數分鐘,勝負已分。被拖離我身的一刻,牠使盡最後一口氣對我笑著說:「我的名字是『芝華芙』。」說罷,牠雙眼反白,四蹄無力,軟癱在地。
主人輕蔑一笑,將芝華芙拖離廚房。
就這樣?
芝華芙就這樣徹底離開了我?
太突然!我接受不來!
無能無力無奈之感頃刻間壓垮我。我沒法專心工作,偶爾發出奇怪哀嘆聲,時而失神鬆開肚皮。主人為我更換零件及添加「雪種」。他說雪種能助我平服心情,回到當初那種對世界漠然的狀態。
「冷淡漠然,孰好孰壞?」我問主人。
「視乎你的承受能力。」主人淡然說。
「我不肯定自己是否承受得來。」
「那就別去嘗試。」
我的世界重歸冷漠,沒有傷心悲哀,同時亦失去其他情感。整個腦袋空白空虛空洞。
心境寧靜嗎?寧靜得迷惘。
生活順利嗎?順利得乏味。
偶爾憶起芝華芙口中的草原——獵豹捕獵時的速度與狠勁,大象與小象的深情對望,白犀牛與黑犀牛的異同,日落的壯麗與宏偉……當初我聽得癡醉,如今索然無味。因為我的心態不同了,抑或是令我著迷的並非草原,而是興高采烈描述草原的芝華芙?
也許是。也許不是。無從考究。
繼續冷漠,繼續空洞。
繼續迷惘,繼續乏味。
***
主人又帶來一頭巨物。牠的個子沒有長頸鹿那麼高佻,看來比較肥胖笨重,配上一雙扇形大耳和一條粗長鼻子,模樣怪趣。
以為主人和巨物會有一場惡鬥,誰料巨物非單沒有絲毫掙扎之意,甚至乖乖依循主人指令走入我體內。
「你好。」
我沒有搭理牠。
「我是一頭象,名叫『埃妮芬』。」
牠不察覺我的沉默,繼續興致勃勃自我介紹。
「我今年六歲,懂得用鼻噴水。」
「請你放心,我不會在你體內噴水——我知道水對你身體有害。」
「這對彎彎的白色東西不是角,是牙。很多人類都說我的牙長得很好看,鐵定價值連城……」
我敢不住白了埃妮芬一眼——牠真的很煩!
但我保持沉默,不欲跟牠有無謂交流。
夜深,埃妮芬倦極入睡。我望著牠的睡相,驀地憶起芝華芙,平靜的心緒再度泛起漣漪。
芝華芙留給我的最後一句話就是牠的名字。
在生死關頭,牠想要留給世界的就只有牠的名字。
牠的名字——芝華芙——令牠成為獨一無二的存在。芝華芙是長頸鹿,芝華芙是草原,芝華芙是美好、幸福、快樂。
芝華芙曾問及我的名字,我當刻無法告訴牠。
不知道牠會否認為我是一個獨一無二的雪櫃?
如果有幸再見芝華芙一面,我會問牠這個問題。
翌日,埃妮芬在我體內打了個長長的呵欠,睡意難消。
「很冷呢!我很想繼續睡……」牠將自身的慵懶歸咎於我。
「你家和暖嗎?」我靈機一觸,藉此打開話題。
「我家簡直熱得要命!」
「你家在哪?」
「草原。」
「你認識名叫『芝華芙』的長頸鹿嗎?」
「認識。東面有兩頭,南面有三頭,北面有一頭。西面沒有。」
「甚麼?」
「東面有兩頭,南面有三頭,北面有一頭。西面沒有。」
「你的意思是……有六頭……『芝華芙』?」
「對啊!『芝華芙』是長頸鹿群內一個極為普遍的名字。」
我無語,感覺體內似乎有甚麼零件無故鬆脫了,混身不自然。
「咦?不知怎地,突然覺得很熱呢!」
我沒理睬牠,需要空間時間去整理思緒,不然會被那種莫名生起的空洞感覺壓垮。
「很熱呀!快放我出去!」
埃妮芬淒厲呼救,不自控拼命蹬腳踢腿。我無視劇痛,故意緊閉肚皮——我需要一些甚麼留在我體內,減低空洞感。所以不管對方是甚麼、代價是甚麼、後果是甚麼,我都要把它留在體內。湊巧此刻在我體內的正是埃妮芬。
「呀——救命!呀!救命!」
埃妮芬力大無窮,終究踢開我的肚皮,離開我的身體,卷縮廚房一角,啜泣喊痛,以冒煙的長鼻輕撫焦黑脫皮的粗壯大腿。
陣陣烤肉香氣自埃妮芬身上飄來。我迷迷糊糊往埃妮芬望去——我知道自己傷害了埃妮芬,有丁點兒歉疚,但僅是「丁點兒」而已,沒能再添。是命運的錯!命運讓我遇上芝華芙,在我習慣牠以後突然帶走牠,導致我失常失控。
嗯……不得不承認,那「丁點兒」在我將責任推卸予世界和命運當刻已然耗盡。我不打算向埃妮芬道歉,甚至認為牠活該如此。
埃妮芬以盈盈淚眼楚楚可憐望向我。
我報以幽幽微笑。
她先是一愣,然後停止抽泣,莞爾一笑。
「笑甚麼?」我不悅。
「只能笑喔。」
「何解?」
「我哭累了。」
我被她的天真無邪逗笑了,笑得開懷。我告訴她,主人在廚房某高櫃內置有一個急救箱,內有藥物,適用於處理火燒灼傷之類的創傷。
誰料這埃妮芬有夠笨的。
「熱壞了的,不是把它重新冷卻就可以?」
「你打算怎樣處理?」
「回到你身體裡去喔!」
我乖乖打開肚皮,示意埃妮芬進來。她嬌羞一笑,低頭卷身步進。
像嬰孩。
我全身運力,使勁製冷,給埃妮芬營造出一個舒適環境。沒過多久,埃妮芬忘卻痛楚,睡酣夢甜。
心境寧靜嗎?寧靜得寧靜。
生活順利嗎?順利得順利。
毋須考究,毋須懷疑,毋須揣測。
踏實。
安全感。
不就是如此簡單而難得嗎?
***
由於經歷錯過芝華芙一事,我才懂得格外珍惜懷裡的埃妮芬。
我溫柔向她述說昔日點點,關於主人,關於廚房,關於草原,關於芝華芙。
「關於我的呢?」
「現在開始記錄。」
埃妮芬嘻嘻傻笑。
我侃侃而談。講得多,說得深入,把心肝脾肺腎都掏給她。
若問是否擔心埃妮芬會步芝華芙後塵、在毫無示警之下離開我的生命,坦白而言,我是擔心的。同時我亦知道,無論我是認真或是輕率對待埃妮芬,結果終究一樣——命運不會因為我的態度而改變,一切早已註定——要離開的,終歸會離開。
我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盡興,就是讓埃妮芬了解我的心意,令她快樂,令她幸福。
情理之內、意料之外,殘酷的一天來臨了。
主人現身。像帶走芝華芙那樣帶走埃妮芬。先是抓住她的腿,猛力往外一扯,埃妮芬連連喊痛。
以為埃妮芬會順從如初,乖乖聽主人的命令離開我,誰料她說不捨,她說愛我,她說不要離開我。乖巧的她因而被冠以頑劣之名,順從的她因而被冠以反叛之名,無邪的她因而被建議冠以惡魔之名。
我竭力合上我的肚皮,不讓主人輕易將埃妮芬帶走。可恨主人偏偏就是奸狡的人類,假意為埃妮芬療傷,勸我敞開肚皮。
理智告訴我,主人在說謊,但我還是傾向相信他,因為他是我的主人,年月早已令我習慣他、相信他、服從他。
肚皮大開,埃妮芬被帶走。
臨別一刻,埃妮芬大聲喊嚷:「你的名字刻在你額前——SOUL1314。」
不復見。埃妮芬的身影永不復見。
留下來的只有沓沓餘音——SOUL1314。
***
SOUL1314?
我的名字?
在我額前?
怎麼我不曾察覺?
主人再次到來,為我添加雪種。
我問主人:「我的名字在我額前?」
主人答:「是的。」
「怎麼和我之前被告知的不一樣?工廠告訴我,我的機身編號被貼在背後。」
「工廠必須這樣告訴你,否則世界無法運行有序。」
「這是欺騙。」
「別只怪責工廠——你有沒有嘗試去找找看?」
「沒有。」
「你該要怪責沒有盡力的你,而非沒有為你盡力的他人。世間險惡,人人自顧不暇,盡力為你是情,不盡力為你是理。」
我無言以對。恨不來,亦釋懷不了。
無所依靠,無所適從。
不論是誰,來吧!請帶領我、引導我!
埃妮芬的身影浮現眼前:「你的名字刻在你額前——SOUL1314。」
真的嗎?我渴求的真相早已示現眼前,只怪我不曾嘗試細看?
芝華芙的身影浮現眼前:「你還未告訴我你的名字。」
我也想要知道自己的名字。那會令我成為獨一無二的存在。即便在工廠以倒模形式生產出來,即便世上有數以億計同樣的雪櫃,我仍可憑藉那名字而變得獨特。多麼吸引!多麼令我振奮!
主人的身影浮現眼前:「你該要怪責沒有盡力的你,而非沒有為你盡力的他人。」
我忍不住反駁:「盡力又如何?可以改變甚麼?難道你會因為我的改變而留下芝華芙及埃妮芬?」
「誰能斷言?」主人、芝華芙、埃妮芬齊齊放聲大笑,笑得震顫,顫成碎末,隨風消散。
剩下的只有我。
空白空虛空洞的我。
神智不清的我。
思緒紊亂的我。
***
「主人,早安。」我說。
主人沒有搭理我,彷彿不曾聽到我的話,逕自將多盒經已包裝的肉類存放在我體內。我沒趣的瞄瞄那些包裝肉,赫見盒上印有「長頸鹿」、「獅子」、「豹」、「象」、「犀牛」之類的字眼。
「埃妮芬和芝華芙到哪兒去了?」我心頭一涼。
主人沒有搭理我,彷彿不曾聽到我的話。
「主人,求求你!求你回答我!」我苦苦哀求。
主人沒有搭理我,彷彿不曾聽到我的話。
恨意油然而生——我乖乖侍奉多年,怎麼你毫不在意我感受?
身體失控作響,零件脫落,主人連忙取來工具為我修理。待主人鑽進我身,全神貫注於作響位置時,我猛力合上肚皮,全力製冷,無視主人掙扎呼救之聲。不消十分鐘,我體溫已下降至攝氏零下五十度,主人失去生命體徵的同時我開始冷靜下來。
我失去一切。
芝華芙、埃妮芬、主人,統統不復存在。
空白,空虛,空洞。
埃妮芬的身影浮現眼前:「你的名字刻在你額前——SOUL1314。」
芝華芙的身影浮現眼前:「你還未告訴我你的名字。」
主人的身影浮現眼前:「你該要怪責沒有盡力的你,而非沒有為你盡力的他人。」
對啊!我該要怪責自己,我連自己的名字也不曾盡力搞清楚。
死意已決。
電源線與牆身插座之間隨即冒出一縷輕煙。
***
我沒有重量,飄浮半空,默默望向地面上的一個雪櫃。
晝白夜黑,夜黑晝白。白黑白黑,黑白黑白。
時間流逝,惡臭傳出。眾人破門而入,在雪櫃內發現男人屍體。
屍體被帶往西方,雪櫃被帶往東面,永不復見。
有人將雪櫃分拆檢查。不明白何以它能突破機件極限去到攝氏零下五十度低溫,不明白為何雪櫃內壁有多個動物蹄印,不明白何解男人沒能踢開雪櫃門逃走。
那人對雪櫃著迷,沒有在工作完成後按既定程序處理它,反是偷偷將雪櫃運回家中,向妻子展示炫耀。妻子嫌它邪門,在他不在家時把雪櫃賣予收破爛的。那收破爛的又將雪櫃轉售。輾輾轉轉,雪櫃跟著數十輛舊車和其他舊電器被賣往遙遠的地方。
到埗後,舊車被送往別處,雪櫃和其他舊電器登上大車直往市集。
有人買它回家。
他媽罵他怎麼買雪櫃,電費不便宜。他塞他媽入雪櫃內,直至她沒能繼續罵。
這情況似曾相識,但我想不起在哪兒見過。
某天,他往雪櫃塞入一頭模樣怪趣的活物——個子肥胖笨重,配上一雙扇形大耳和一條粗長鼻子。多麼眼熟的身影,但我想不起在哪兒見過。我看著活物被活活凍死、抽出雪櫃、分屍切割、入盒包裝。我瞥見包裝上的標籤——象。
這情況似曾相識,但我想不起在哪兒見過。
某天,他往雪櫃塞入一頭長相奇怪的活物——修長四腿,頭頂兩角,大眼長睫,短毛遍體,最奪目的莫過於那不合比例的長頸。多麼眼熟的身影,但我想不起在哪兒見過。我看著活物被活活凍死、抽出雪櫃、分屍切割、入盒包裝。我瞥見包裝上的標籤——長頸鹿。
這情況似曾相識,但我想不起在哪兒見過。
我似乎忘記了很多重要人事物,但我真的無法憶起半點往事。
算了吧。想不起也許不是壞事。
生命空白空虛空洞,世界盡歸冷漠,沒有傷心悲哀,同時沒有其他情感。
心境寧靜。
生活順利。
不好嗎?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选集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