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感染了《罪與罰》中的冠狀病毒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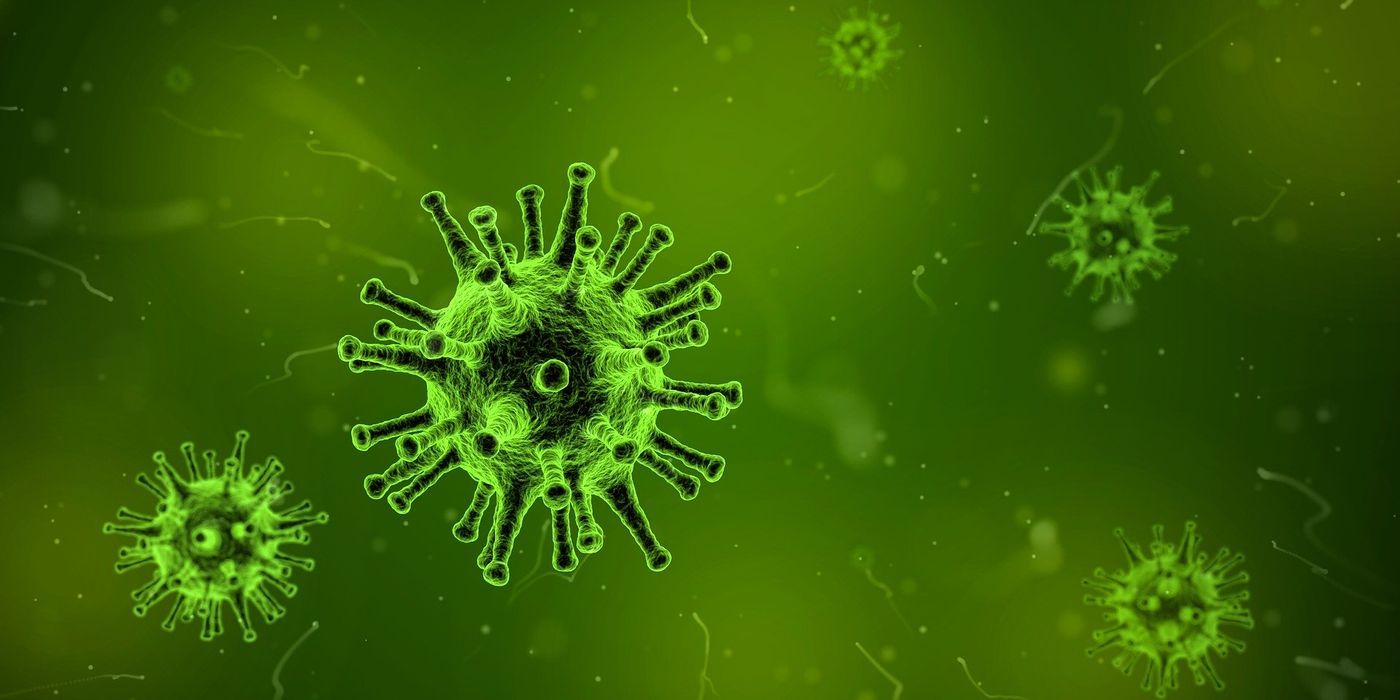
俄羅斯小說家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的名著《罪與罰》的尾聲描述了一種奇怪的疫症,這種疫症是這樣的:
「全世界都因一隻來自亞洲內部的不知名和可怕的瘟疫而變得荒涼。這瘟疫傳遍整個世界,除了部分『選民』之外,全都被消滅了⋯⋯被傳染的人會立刻瘋掉,但奇怪的是,患病者會同時強烈地相信自己判斷的正確:他們從未曾相信自己是如此充滿智慧、擁有縝密嚴謹的智性或科學的結論,和自己道德上的觀察是如此正確。整條村子和市鎮,整個人口都受感染,並因此失去他們的理性。他們無法理解旁人,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惟一擁有真理的人。他們看著他們『未開化』的鄰舍時會搥胸舉手大哭。他們無法和旁人在任何一點上達成共識,也不知善惡,他們在憤怒中互相攻擊並彼此殺害。他們組成軍隊,但一旦成形,他們就將對方撕碎。」
這「疫症」是否有點似曾相識呢?
香港的《罪與罰》「冠狀病毒」
若我們細心觀察香港的政治評論環境,不難發現這種「病毒」其實已存在於香港頗有一段時日:偶爾你會留意到某些自命不凡的人,他們帶著一副「世事都被我看透.jpg」的鄙夷態度(有時還混以跳躍甚至缺乏的邏輯),嘲笑旁人看似愚蠢的善良,批評旁人看似徒勞無功的抗爭,和瘋狂攻擊和他們稍有不同的意見。彷彿這個世界上,只有他們才是「惟一擁有真理的人」,只有他們才「充滿智慧、擁有縝密嚴謹的智性或科學的結論」,只有他們才能作出準確的「道德上的觀察」,而旁人都是「未開化」的:因此,旁人必須聽從他們每每缺乏證據、邏輯跳躍甚至自相矛盾的論述和判斷,因為他們是如此的超人一等。
更有趣的是,這些人不但會瘋狂咬嚙和他們不同的人,他們亦會如 Dostoevsky 所說,會不斷的「在憤怒中互相攻擊並彼此殺害」:不少昔日的同路人和親密戰友,今天已是要「皇天擊殺」的死敵。倘若你一個不留神,將你撕碎的,可能不是你的敵人,而是這些你曾認為和你一樣熱血奮鬥的同路人。
當然,正如 Dostoevsky 清楚指出,這些人其實並不如他們對自我判斷那樣擁有高超的智慧和道德判斷,相反,他們是「失去理性」和「瘋掉」。《罪與罰》某程度就是描繪這種「瘋掉」帶來的後果。
我稱這種病毒為「冠狀病毒」,是因為這種自以為識窮天下,站於最高的道德高地的症候,既有這些人「自以為冠軍」的意思,也有他們「沐猴而冠」、看似金玉其外但其實敗絮其中的意味。很有趣的是,真正高瞻遠矚的人是不會有這種「冠狀病毒」的,最易被「感染」的,反而是一些本來自卑心甚重的人,一旦他們找到認同他們的志同道合者,就會開始聯群結黨,互相吹捧,直至最後連他們自己也相信,自己是與眾不同的「救世主」:我擁有絕對的真理,你們其他的都是其蠢如豕的次等人。極度的自卑催生極度的自大。
我對獵巫式地找出這些人沒有多大的興趣(這是某些人很喜歡的活動)。我更有興趣的是,在如今抗爭的大氣候中,為什麼我們要提防這種「冠狀病毒」?
抗爭就是要「和而不同」
這是因為抗爭從來不能靠圍爐取暖而達致的,相反,由於我們要盡量團結社會上的人,我們無可避免要和那些和我們不同的人對話和合作:和理非要和勇武攜手;前線的勇武要靠後勤的急救和物資隊合作;手無縛雞之力的所謂「知識分子」或許擅於梳理運動或政府的盲點和策略,但這些策略若忽略街上善於和黑警打游擊的前線抗爭者的洞見,其實只是紙上談兵。在整這個龐大的抗爭群體中,彼此間總有不少的「不同」,而這些「不同」可能始終都不能融和(reconcile)。但由於沒有人能獨力完成抗爭的目標,我們和這些與我們不同的人合作,然後期望在合作中將一切融和 (synergise),令 1+1 > 2。
在如今以弱敵強的抗爭中,這樣的胸襟和合作尤其重要:若我們團結尚且未必能勝,何況在互相猜疑中彼此攻擊?這只會給予我們真正敵人逐個擊破的機會。因此,破壞團結的人,不將其他抗爭者視為手足的人,在運動中嘲諷、攻擊、令人洩氣(demotivate)的人,無論他們的話說得多動聽,無論他們看起來有多麼高瞻遠矚,他們都是我們需要提防的人。
這些看似是老生常談,但身染《罪與罰》式的冠狀病毒者,卻每每忽略。
除了策略上有互相合作的必要外,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掌握資訊和視野的有限。我們每個人都受制於我們身陷的處境,令我們對事情的判斷有所偏差。這樣的偏差,只能透過和旁人開誠佈公和互相尊重的對話中被糾正。若我們永遠以為自己是「惟一擁有真理的人」,我們永遠都只能被困於自己的偏見(prejudice)中。
某程度上這也是為什麼民主社會比起獨裁社會更穩定和進步的原因:一個人,無論他是如何如天縱英明的「聖主明君」,都總有其偏見和犯錯的時候:遑論每個人的私心和絕對權力帶來的腐化。民主社會不需要什麼皇上、國師和教主去帶領我們前進,我們只需要每個像我們一樣平凡的人,在對彼此的尊重中對話,尋求共識,讓社會解決問題和進步。
結語:你感染了《罪與罰》中的冠狀病毒嗎?
當然,在這一切的討論中,最重要的問題或許不是「他(指一指旁人)有沒有感染這種病毒?」,而是「我有沒有感染這種病毒?」:我有沒有自以為識窮天下,或擁有最正確的道德判斷,而令我拒絕和別人對話和自我糾正呢?我有沒有因為別人和我的稍有不同,就攻擊、嘲諷和說些使人洩氣的話呢?我懂得怎樣尊重和我不同的,甚至欣賞旁人擁有而我沒有的長處呢?
Dostoevsky 沒有直接討論這種病毒可以怎樣得到治療。但我想治療,起碼在理論上,其實並不為難:走出自己的迴音室 (echo chamber),敞開自己的胸襟,積極和我們不同的人對話甚至合作,並在過程中學習從旁人的角度和觀點看一些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當然,還要接受自己的不足,明白這些不足並不是自卑的理由。
當然,這些都是知易行難,但一切都始於微小的第一步。但願我們能起碼踏出這第一步。
(歡迎網上廣傳)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