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蟻想【修訂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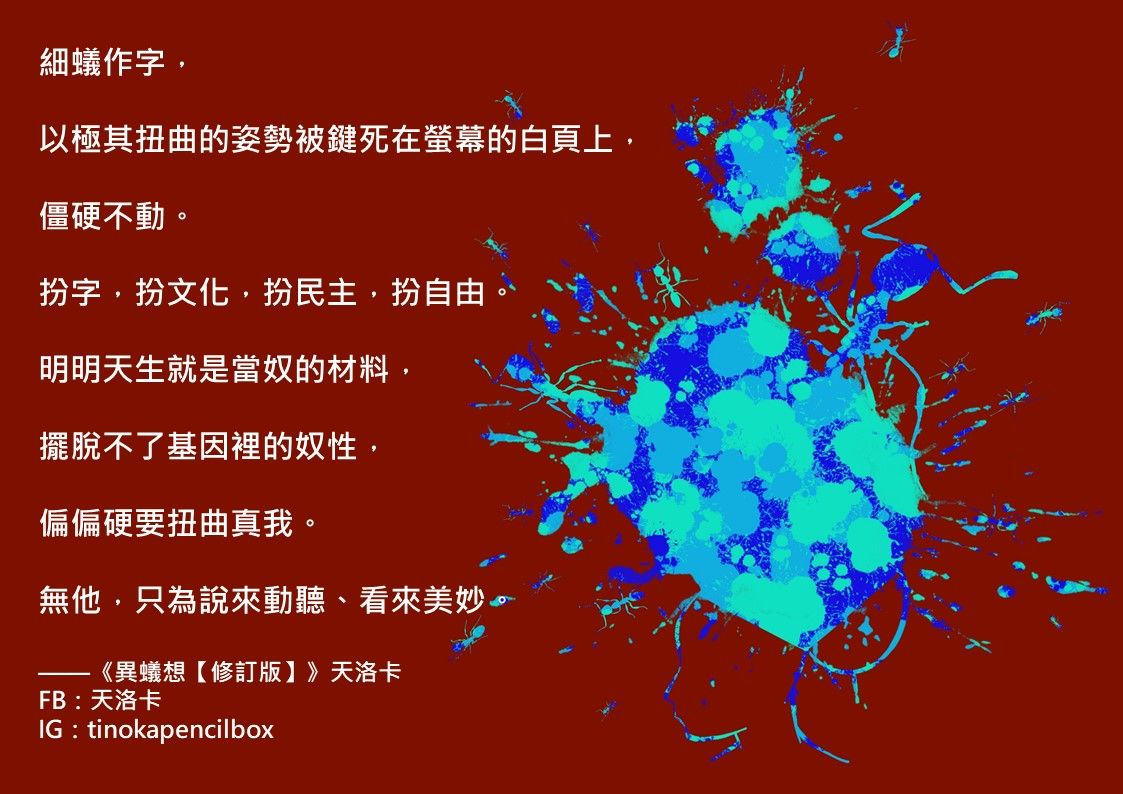
天亮,上班。
擠進人山人海的車廂,心是難得的平靜。看著人們專注把玩手中的電子玩物,我更覺異常安全。畢竟,好不容易才能擺脫熟人的注意。
車廂一如往常,平穩中帶輕微搖晃,教本已帶睡意的乘客更為昏昏欲睡。有些嘴饞的人不理會廣播的呼籲,繼續進食,令人側目。食物的細碎,像沙子一樣,在人們毫不注意的情況下,悄然掉在地上,再被無意地踏個粉碎。在接著的數個車站,人們再肆意加以踐踏,令碎粉再度粉碎。
到站了,我有意無意地繞過人羣,「不經意」踏中那些有數隻小蟻的食物碎粉,心中是一陣少有的快意。幕門關上,我回頭望進車廂,想要看看被我蹂躪過的碎粉和小蟻,但列車經已開駛。
看不見,罷。
天黑,下班。
身心俱疲。好不容易才與同路的男同事擠進車廂,繼續講上司的壞話。
「有蟻。」男同事突然指著快由我鞋面爬到小腿的一隻小螞蟻。
我呆了。腦海中一片空白。不!有一個很遙遠的身影。那是誰?我看不見……我不想看見……
「啪」的一聲,男同事一手拍在我的小腿上,那隻螞蟻——扁了。
「沒事了!」他笑了笑,問我:「你很怕小昆蟲?」
「不,只是怕蟻。」我感覺到,我的唇還在顫抖,卻仍勉力一笑。
小蟻的身體輕於鴻毛,牠的屍身在我小腿上留下重於泰山的黏膩感。明明體液不多,為何會覺得黏膩?不欲多想,不敢多想,怕會從腦袋的深淵引出可怕的蟻群。
好比佛地魔的名字,不能言喻卻長存於心間,帶來莫名的恐懼。
蟻群早已鑽進我的腦袋深處,以此為巢,產卵育兒。幼兒破卵,食我心智,開彊闢土。留下牠們的意志,作為粉飾巢穴的材料。
團結就是力量!為族群服務!分工合作,各施其職!安天命,守本分!不要問族群可以為你做什麼,你應該要問自己可以為族群做什麼!
蟻群眼中的賞心悅目,是我腦海中的黏膩感。像鼻涕,漿稠濃糊,混濁渾沌。拖曳我的身軀,限制我的思想。沉重非常,可又無以抵抗。
很可怕的蟻群。我從不敢正視牠們。視而不見,並非最好的解決方法,卻是最好的自欺手段。
插匙,開門,踏入家門。
一隻人高的蟻披著圍裙,正在煮飯做菜。飯菜糊糊的,倒人胃口。
牠命令我吃下所有。我不敢違抗,硬著頭皮,哭喪著臉,吞下滿口黏膩。
噁心。
「好吃嗎?」牠問。
「好吃。」我不敢交出其他答案。
***
辦公室裡,午飯時間。
為節省資源,部份天花燈盤會被關掉,空調溫度亦會被調高至攝氏二十五度。辦公室頓時暗了大半,空氣變得侷促,稍帶窒息感。屏風隔開留在辦公室用餐的同事們。大家留在自己的座位上用餐和消遣。
甲小姐正在上網看劇,劇情不外乎一哭二鬧三上吊的催淚套路;乙先生在打盹,鼾聲像豬嚎;丙小姐上網找外遊地點的資料,不自覺地笑不攏嘴;丁先生仍在享用他那巨型飯盒。飯餸窩在膠盒裡大半天,質感甚為軟糯糊漿,略帶病態的慘白;戊小姐……
我背靠軟綿綿的咕𠱸,安分地半躺電腦椅上,披著薄外套,呆望兩呎乘兩呎的石膏板天花發呆。我頭頂上的石膏板板塊看來是最大最方的,望去辦公室盡頭,那邊的板塊似是細小的梯形。天花骨為平白的天花畫下美麗的距離感。雖偶有幾個仍然亮著白光的燈盤作調劑,可惜無補於事,冰冷不減。一格一格的,人工化的,機械似的。
大家是披著有機表皮的機械,是螞蟻。具有個人特色的面目逐漸模糊起來,倒模一樣,沒能分辨你我他。當大家企圖以不同的方法去活出自己的生命,卻渾然不察那套被植根腦袋的思考模式。千迴百轉,最終仍然盲目地將畢生奉獻予族群。勞碌營役,換來兩餐吊命。未死,就可以繼續奉獻,沾沾自喜說:我的生存真有意義!
驀地,一隻抬著餅碎的螞蟻在我手背上爬過。生起憐意,我把手輕輕放在枱面上,讓牠自然而然的爬走。看著牠和牠的意義消失在牆角縫隙,我感到自己也隨之隱去。
屏風後,埋首工作。
指頭飛快在鍵盤上舞動,噠噠作響。
字細如蟻。
細蟻作字,以極其扭曲的姿勢被鍵死在螢幕的白頁上,僵硬不動。扮字,扮文化,扮民主,扮自由。明明天生就是當奴的材料,擺脫不了基因裡的奴性,偏偏硬要扭曲真我。無他,只為說來動聽、看來美妙。看!以生命構建的字體果然不同凡響!
我嘴角上揚,內心舒爽。鍵.死.牠!
一陣濃郁的俗氣香水味忽爾從遠處傳來——女上司人未到,氣先到。「你!」她來到我的身旁,怒氣沖沖,乾脆利落地將厚厚的文件拍在我枱面:「怎麼可以錯得這樣離譜!」塗了桃紅色甲油的右手食指指甲連環使勁戳向「錯處」,戳出幾個嚇人的微坳。
我托托沉重眼鏡框,將礙事的長髮架在耳背,湊近細看可憐的錯處:「這個銀碼是依據乙先生給我的數據填寫的……」我熟練地從旁邊的文件盤抽出黃色的文件夾,拿出乙先生給我的紙頁,遞給上司看。怕她看不懂,我還在旁給她詳細解釋。
女上司臉色玄青,瞄向乙先生。乙先生馬上上前辯解,推說是戊小姐的解說誤導了他。戊小姐想了想,將責任卸給甲小姐。甲小姐不加思索,將丁先生拖入這趟渾水中……兜兜轉轉,矛頭竟指向女上司最初發出的某個指令。
女上司老羞成怒,當眾將我罵個狗血淋頭。同事們心知犯錯的不是我。無奈,他們違逆不了奴性的感召,對不公不義變得麻目,齊齊目送我上斷頭台。繼而將這粉飾為必然的事情、生存的定律,沒人需為此生起歉疚或同情,省下道歉或安慰說話暖肚。
我的思緒出體神遊,繞著女上司打圈飛,帶笑靜觀她的醜態。時間流動減慢,以便思緒看清每一細節。脹紅了的大塊肉臉上,是奇大的圓眼。搽了桃紅唇膏的兩片薄唇毒辣不饒人,兩隻大牙間,偶爾噴出臭人的唾液,向眾奴傳遞指令。碩大體型冠絕全公司,特別是腹部和臀部,肉騰騰的、圓潤的,該是很好生養,能夠百子千孫……
漸感沒趣,我的思緒先行遠飛,飛至女廁去。靜待。直至麻目的身體前來會合。
心神合一之際,一隻大蟻湊巧路經廁格。我毫不猶豫,一指按扁牠的頭。頭部受壓向下栽,肉騰騰的、圓潤的腹部反倒順勢往上翹,幼小的觸肢連掙扎的時間也沒有,就此永遠凝住。
詭異的快意透徹全身,毛管直豎,頭皮發麻。
我笑了。為牠的遭遇而笑。
***
下班,清吧內消遣。
店家欲以昏暗燈光打造情調。可在我看來,這更像成本低廉的地底礦洞的老舊照明燈。竭盡全力,也照不出應有的亮度來。勉強看到距己十步的前方,我需要依靠前方男同事的古龍水氣味去辨別路向。
九曲十三彎。好不容易,我們在位於一隅的小梳化坐下。我從餐牌挑了橙汁、煎雞翼和炸魚柳,他要了雞尾酒和花生小吃。摘下眼鏡,看不清世界,我方能開懷起來,好好放鬆。邊吃邊喝邊聊天,罵天罵地罵上司,好不痛快。
酒過三巡,醉態浮現於男同事臉上。我勸他不要再喝,馬上回家休息去。他不依,反而多點一杯雞尾酒,硬要我飲。
「你不是只怕螞蟻而已嗎?為何現在也怕酒?」男同事指著我的橙汁哈哈大笑起來,笑我孩子氣。笑的時候,兩隻門牙顯得不合比例的大,甚至略略變型,像一對彎月。
「我不大喜歡喝酒……」我怯怯推卻。怕酒,也怕他。是照明不足的緣故?是摘下眼鏡的緣故?我竟看見男同事不成人形。黯黃燈光糢糊地勾勒出他的奇特身影:頭小,胸小,腹大。
「還是……」他以極其鬼魅的姿勢地趨向我,湊近我耳邊:「你根本不會喝酒?」不知他是有心或無意,舌尖碰到我的耳珠,留下丁點濕潤,散發淡淡酒氣。
我全身泛起一陣酥麻,思緒亂轉亂竄。
「螞蟻是用分泌物的氣味來進行交流的。」中學的生物科老師不懂授課,課堂很沉悶。
見我呆住,男同事放膽張口噬向我,予以強攻。
「螞蟻用兩個大牙叮咬的方式進行攻擊或自衛。」生物科老師如斯說。
雙唇交疊,雙舌互纏。他在我口腔留下微酸。他說,他喝的是「威士忌酸酒」,是一款經典的雞尾酒。
「螞蟻叮咬時會分泌出蟻酸。」生物科老師的教誨,我永世難忘。
威士忌、檸檬汁、砂糖、蘇打水混合起來,成為怡人的清新。我喜歡這徘徊於清醒與醺醉之間的芳香,好比掙扎於自由與奴性之間的耀眼花火,誘人,傷人,殺人。
一口氣乾掉一整杯。
醉倒。
其實,真正的我只是一個渺小的人類。不過會偶爾做白日夢,幻想自己是一隻蟻,過著那種沒頭沒腦的生活。那種生活很乏味,只懂遵循本能的驅使,為族群盲目付出。無他,這就是生存!
還是……
其實,真正的我只是一隻螞蟻,不過會偶爾做白日夢,幻想自己變成人類,過著那荒唐無稽的生活。那種生活,是有目的的付出,帶有希望的付出。每天朝著那所謂的「希望」跑,多奢侈!無他,這就是意義。
意義,在哪兒?
哪兒?伸手不見五指,男同事的氣味籠罩著我。哪兒?他六肢並用,爬上我的身,不停遊走於每吋肌膚。哪兒?腥臭的觸角四處探索,想要找出通往洞穴的道路。
婚飛。半透明的翼身折射出謎樣虹光,為沉悶的周遭添上一份誘惑氣息。血脈沸騰,靈慾飛昇。幼長的薄翼亢奮張開,拍動聲浪不絕於耳,重覆又清脆,擁有催眠的魔力。明知是萬劫不復的境地,偏偏抵受不了誘惑,一頭栽進渾水裡。
交尾,著地。他是我的愛,我的選擇。我緊緊擁著他,盼在他失去知覺前,盡量給他一絲溫存。可悲或可喜?他的生命只為尋歡而誕,壽命終結於極樂之時。該笑或該哭?我的雙翼悄然脫落,說明我已進入生命的黃金時期,有能力落地生根,繁衍後代。但,我的自由同時告終……
翌朝,我被食物的香氣喚醒。披著被單,躡手躡腳走到房外去。男同事正手忙腳亂地在餐枱上延開一頓豐富的早餐。
「早晨……」他的笑容帶點靦腆:「來吃吧。給你買了粟米粥,質地綿綿的。」
我沒開口回話,衝前緊緊抱擁他,懶理掉落地面的被單。
我以為他已然死去,有如交配後的雄蟻。
***
假期,醫院。
媽無故在客廳昏倒,撞傷了頭,被送到醫院。病因未明,有待檢查報告出爐。
家中各人淚眼漣漣,圍著媽的病床,十分憂心。這種沉重氣氛,令健壯的人也難免感到窒息。難怪,媽向來心廣體胖,在醫院躺了沒兩天,已然雙目無神,瘦骨如柴。
媽是個典型的傳統婦女,家庭觀念甚重。她身體力行,竭力維繫家庭完整,獻出一切:金錢、青春、時間、前途、心血、個人自由……每個認識她的人都會稱讚她是個好媽媽、好妻子、好姐姐、好女兒。但我從來她不覺她是個好「人」。
她不是人。她是蟻。
媽是家庭裡的蟻后,沒有統治權,但各人自然而然會以她為家庭核心,萬事以她為先。在媽面前,家人之間即使心病再多,大家總會給她幾分薄面,假笑暫泯恩仇。
家庭和睦,聽來是多麼美好。但這份美好全建基於媽的存在和努力。如果她不復存在,這份美好還會繼續流傳下去嗎?若否,這份美好不就是虛假的幻象嗎?換言之,我們全都被媽困禁在這虛假的美好幻象當中。
撫心自問,我不想媽出院。
我要光明正大地直斥爸的不是,罵他賭蟲上腦,連累家庭;我恨不得拆穿姨的偽善面具:律己以寬,待人以嚴;我要搗破婆的心房,告訴她,你的寶貝兒子早已拋棄你,不要再惦記他。望望你一直忽視的女兒(媽),她才是每天照顧你、忍受你臭脾氣、為你花心思的人;我要和妹妹一起商討未來大計,那些媽一直反對我們付諸實行的大計……
我歹毒嗎?我自私嗎?會比媽更自私嗎?她以「維繫家庭」的名義,強要一幫合不來的人日夕相對,硬要大家生吞一切怨懟。哪管你消化不良或是甚麼的,總之,吞!
我不明白,為何明明合不來,還要在一起?為了沒能選擇的血緣關係?那點血脈會比眾人的快樂和自由更重要?組織家庭、組織社會、組織族群,是為了方便人類溝通、交流,將人類文化推上更高更好的位置。現在媽卻本末倒置,為了組織家庭,硬要所有人留在不好的境地裡原地踏步。
我願意顧及媽的感受,並非因為我愛她,而是因為我可憐她。
她是表現奴性的極致。奴性入骨入𩪷入基因,為活而活,為行傳統而行傳統,為組織家庭而組織家庭。她沒有錯,她只是盲目跟著社會的步伐前進而已,沒有思考過那是否適合她。
嚴格而言,媽是一個受害者。和大部份人一樣,她自以為正在活出只屬於自己的生命,卻渾然不察那套被植根腦袋的思考模式。千迴百轉,最終仍然盲目地將畢生奉獻予族群……
「我覺得……」今天,媽的話變得斷斷續續:「自己……」
大家都屏息靜氣,深怕這是她的最後一句話。
「自己是……一隻螞蟻……」她的聲音輕如柔絲,但我知道大家都聽得很清楚。
死寂。
出乎我意料,她竟講出人生中最清楚的一句話,不論是肉體還是心靈上。
每次望著媽,心中都起了不能言喻的感覺。我的腦海中,只浮現出一隻螞蟻的身影。她根本就是一隻螞蟻。
一隻螞蟻在做菜煮飯、洗衣拖地、燙衫抹窗……牠看來和藹可親,不具侵略性,卻偏偏是把我的個人意志摧毀得最嚴重的傢伙。
久而久之,我每次一見到她,便會掉頭走。
***
某高級私房菜館,跟客人開會的場地。
平日女上司外出開會應酬,喜歡帶老練的乙先生或戊小姐同行。但今次卻挑了我一起去。開席前,客人和女上司有說有笑,氣氛輕鬆。拿出合約,以閒聊方式討論細節時,客人和女上司同樣笑容滿面。上菜時,客人喜上眉梢,難掩興奮,女上司卻僵住了。我,毫無掩飾,尖叫出來,從餐椅彈起,連退數步,直至碰到活動趟牆板。
客人瞟向我,邪笑道:「第一次食蟻宴,感到嘔心是正常不過的事。」見慣風浪,沒有絲毫不悅。
我立在原地不動,震顫不已。女上司收拾心情,首次對我露出和顏悅色的笑容:「來試試,試過就知道是好東西。」她向我招手,示意我回到餐桌旁。「我起初也是抗拒得很,但放膽一試後,卻發現這是人間美食,欲罷不能!」女上司的口吻像媽,像那隻扮人的蟻。
天旋地轉,眼前畫面扭作一團。我身處蟻巢當中,面前有兩隻人高的巨蟻,一雌一雄。兩對大眼齊齊掃視我全身上下,逼人目光快要擠爆我心臟。恐懼掏空了我,腦海裡空盪盪的。牠們的花言巧語一再迴繞,從腦袋深淵引出可怕的蟻群。大咬大啃,蠶食我的心智,留下牠們的意志。
我沒作聲,任由體內蟻群放肆地吃喝玩樂、組織家庭、創建社會、發展文化。牠們驅使我乖乖回到座位,一口氣灌下半碗白蟻湯。
好吃嗎?
好吃。
「你有看《天與地》嗎?」雄蟻吃了一口紅蟻炒蛋。
「有。意識挺大膽的!人吃人!」雌蟻滿口黑蟻殘肢。
「這個問題,我問過很多朋友,大部份人的答案和你的一樣。但在我看來,『人吃人』情節根本算不上甚麼一回事。」雄蟻擺出權威口吻,在雌蟻面前大發偉論:「『人吃人』每天不斷上演。在生活裡的各個層面、以多種方式活現眼前。不一定是吃人『肉』才算得上吃人,食人『心志』也是吃人的其中一種方式。」說得口乾,雄蟻呷了一口黃蟻甜湯。
「絕境下,三位男主角吃了重傷好友,維持生命。獲救後,男主角們因為好友的死而性情大變,走上歪路,毀掉人生。簡言之,好友失去了生命(身體),精神卻長存於男主角們心裡;男主角們的身體雖繼續活著,心志卻被罪疚感反噬,沒能以他們本身的真實性情活下去……
世事無絕對,大都是觀點與角度造出來的假象。我與你,少數與多數,個人與世界,哪能分得清清楚楚?」
「這麼推想下去,到底是誰吃掉誰?誰被誰吃掉?那真難懂!」不著痕跡的一句讚美,雌蟻注定能夠吃掉雄蟻。
好不容易,飯局完結,合約簽妥,我和女上司恭送客人上坐駕。車影遠去,女上司和我漫步大街上。
「別怪我沒事先通知你。」女上司從手袋掏出一包酸甜小零食,大方地分了三粒給我:「乙先生吃了一餐,戊小姐吃了一餐,你吃了一餐,我吃了三餐。」
我先放了一粒入口。不甜,很酸,酸度足以將蟻群和我一併溶掉。
「總有一天,我會習慣。」女上司也吃了一粒,企圖將她自己溶掉:「我是這樣告訴自己。」
「只要習慣了,我就可以毫不猶豫,吃得更多,簽下更多訂單,得到更好的待遇,過更好的生活……」女上司又吃了一粒小零食,溶掉披在身上的人皮,露出蟻身。「好好的活著,算得上奢侈的事嗎?」
我再吃一粒,溶掉對牠的厭惡。我吃下最後一粒,溶掉對世態的耐性。
我辭職,我說。
***
我沒有回家去,直接溜到他的家去。我和他之間已沒有同事關係,我可以乾脆利落地喚他「男友」。對我的突然造訪,他不解,卻沒有多問。呵呵哄哄,給我吃零食、玩遊戲機、穿他的睡衣、睡他的床。
一輪熱吻愛撫後,男友進入極度興奮狀態,將我壓在胯下,沒注意到我正在放空自己,思緒飛往遙遠的他方去了。
産房內有一張床,床上有一隻蟻后。她的腹部異常腫脹,疼痛非常,是産婦們所講的十級痛楚。厲聲喊痛,觸肢下意識地在空中揮舞,似乎臨近生産時刻。
「生產就是會這樣痛。」我以冷眼回應牠的苦痛:「長輩們沒有告訴你嗎?」
「長輩們只告訴我,這是命運!是必然的,不得不接受。」牠低頭看著腹部,兩肢隔著下腹撫摸著卵狀的孩子,思考著命運的必然。「我生來就是為了生產。除了生產,我的存在沒有其他意義。」
「這並不是必然的。只要沒有和雄蟻婚飛交尾,你就不會懷孕。」我戳破長輩們的謊言,戳破牠整輩子的信念:「即使你當不成蟻后,你也可以當工蟻。」
牠嗚咽起來,感到受傷。我心生歉意:我給牠看見了擦身而過的選擇,在一切已成定局的時候。哭聲未落,淒楚慘叫聲隨即補上。蟻卵以排山倒海之勢自牠腹部小穴飛瀉而出。不消一會,整張床上都是蟻卵,恐怖非常。但牠的身體卻沒停止的意識,繼續排卵。蟻卵迅速攻陷整個産房、整間醫院、整個世界。
我驚恐萬分之際,耳邊卻傳來蟻后的哀音:「他朝君體也相同!」
床上的我驚叫,但男友卻誤以為我也感到興奮,於是更用力……
我懶理家人的反對,繼續留在男友家住。他的家說不上鬆動,僅僅夠兩個成年人居住。這份壓逼感,帶點侷促,卻意外地為我提供莫名的安全感。就像走在熟悉的蟻路上,不需選擇,不需思考,不需擔心。按著既有的指示,一直前行,就會去到預期的地點。輕鬆,簡單。
我挨近窗戶,望向地面黑壓壓的頭頂。我分不清那些是人頭或蟻頭。
我一直鄙視活得像蟻的人,恥笑他們沒有自由意志,終身困在無形的樊籬當中。此刻反觀一切,我不也是將自己困在另類的樊籬當中?為了不和他們一樣,我限制了自己的行動。像蟻后,餘生只能活在巢裡。
自那天到來男友的家後,我沒有離開過單位。怕要面對隨波逐流的蟻,和牠們相處、溝通。思想是高傳染度的傳染病,可以經由言語、文字、圖片、暗示、氛圍等途徑傳播。避無可避!
我忽爾靜默下來。茅塞頓開。
根本早於懂性之前,我的腦袋已被蟻群佔據。可能是新品種的蟻,也可能是未被其他人發現過或命名過的蟻。牠們的排他性奇高,所以我對身邊的所有蟻群那樣敏感……
病入膏肓了?沒救了?
不!我才不要和那隻可憐的蟻后下場一樣!
我不能妄下定論,不然會中了蟻群的詭計。我告訴自己,只要未死,就有得救可能。可是,要怎麼救?火燒蟻?煙燻蟻?水淹蟻?毒殺蟻?
靈光閃現。我想起了客人和女上司的對話。「人吃人」只是個例子,同類相殘才是真相!為了減少競爭,每個物種均有相爭相殘現象。自己最了解對手的同時,對手同時最了解自己。最懂殺人的是人類,最懂滅蟻的是蟻!
我走到廚房去,金睛火眼,環視四周。
牆角有隻蟻路過。
我將牠放入耳窩。
期待漁人得利之日。
***
靈堂裡,相框上,是亡者最愛的黑白照。明眸酷齒,烏髮雪肌。像人,是媽。媽在醫院裡待了三個月,可惜等不到適合的器官作移植。也是的,不知多少病者等了多少年,也輪不到一個器官。何況她只是等了三個月……
我一再向來賓欠身鞠躬。到來致意的,是蟻。和我一起站在主家席的,是蟻。躺在棺木裡的,是蟻。滿堂是蟻。我沒有絲毫驚懼,因為我已習慣蟻的存在,包括體外的蟻和體內的蟻。
體外的蟻與我比較相處得來。在遠去的那些年,牠們曾經是人,保有些許人類的特徵。牠們善於假扮人類,扮思考,扮自由,扮公平,扮大愛。牠們的偽裝幾近完美,唯獨是極強的「排他性」沒能完全被遮掩。若我的真正身份一旦被揭發,我勢必陷入萬劫不復之境。
我不斷告誡自己,必定要忍。只要忍過去,不拆穿牠們的假面具,就不會遭受攻擊。這可不是易事。我畢竟不是牠們的同類,要做到和牠們行徑一致,必有一定難度。
幸好,我還有體內的蟻。在我體內,有處於敵對狀態的兩群蟻。牠們為爭奪更多資源,不停戰鬥,將我的身體各個部份當作戰場。當某些身體部位感到劇痛時,我就知道,牠們正在那兒開戰。戰後,無論誰勝誰負,亡者的屍體都會腐爛分解,化為黏液,滲入我身體各處。牠們的意志會隨著黏液成為我的一部份。
相比昔日的我,現在的我有點兒像蟻,無論思考模式或行為習性皆然。但我清楚知道,我只是扮蟻的人。
喪禮過後,我和妹並肩行。
我不知該視妹為她或牠。半人半蟻的狀態,該怎麼分類?我不懂。妹曾經和我同聲同氣,對家庭的無理束縛同樣不滿。惟在媽入院後,妹的態度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變,說甚麼「血濃於水」。我沒贊同,亦沒反駁,單純的無話可說。
彼此相顧無言,卻因一隻小蟻而開始對話。
「小心!」妹吹走我手臂上小蟻。「難道是在靈堂裡拈來的?」妹說,剛才在靈堂主家席附近看見很多蟻,卻又不敢清走牠們。傳說,亡者能夠附在小昆蟲上。
「可能吧。」我淡然一笑,心裡歡喜妹記得我怕蟻。沒料到,妹仍記得以往的我。
「這裡又有一隻蟻!」走沒兩三步,妹突然又指向我的衫尾。
我瞄了瞄,一指彈走小蟻。我知道蟻從何來:來自我身體內。近來,不時發現有少量蟻會隨著我的糞便和尿液排出體外。我估計,牠們已遷居至我下體一帶。偶有幾隻發現了出入口,好奇到外邊的世界看看。
「咦?那裡又……」妹的吃驚神情提醒了我。若在這話題上繼續擾攘,恐怕妹會發現甚麼端倪。
「我去整理一下,不用等我。」我匆匆轉身離開。
妹不會明白我,我亦不打算要妹明白我。
有時候,我在想,奴性為何得以如此猖狂。天性使然?僅此而已?不。因為清醒會痛,痛感來自自身的無力。看見世態的扭曲,卻沒能改變,更遑論救走在意的人。天天在無間地獄消磨身心靈,由呱呱墜地一刻,直至與世長辭的一剎。無力感,殺人不見血。
或許,我不該好管閒事,放手讓那些被蟻群玷污的人繼續以奴性活出生存意義。
正如男友一樣。
三日前,男友發現了蟻巢所在地,發瘋似的拖我去見醫生。我不依。
「你會死!」他愛我。
「人總有一死,無需懼怕。與其活得苟且,我寧願死得清醒!」我愛他:「讓我們各自選擇自己的快樂吧!」
他呆住了。
拍拖前,他提及過自己的夢想:他不甘心整輩子看人臉色,誓要開公司當老闆。拍拖後,萌起結婚念頭後,他說要安安份份找份高薪工作,給我過安安穩穩的生活。賺錢養妻活兒,孩子要當醫生或律師……他擁我入懷,興奮無比地說了很多夢話,做了很多美夢。夢很美,美得可笑。我心懷歉疚。因為他的改變是基於對我的愛。他為了我而扭曲了真正的自己,不成人形。
他仍然呆住,隨我逕自走過他身邊,鑽出蟻巢。
他經已徹徹底底成為一隻蟻。我心痛,但祝願牠永遠活在美夢當中,快快樂樂。
***
賣掉身上所有值錢的東西,扔棄身份證,我的人生自此完全脫軌。
衣。每天穿著同一套衫褲鞋襪,直至髒掉、臭掉才去找替換,不再擔心別人看待我的目光;食。世上總有浪費食物的人類。我把他們吃剩的食物清掉,造福世界;住。天氣不錯時,幕天席地。天氣欠佳時,隨意找個公廁躲進去;行。多數靠雙腳。惟有時候欲過海看風景,才逼於無奈搭鐵路。
搭鐵路,算是和舊日生活最相似的一刻。時空交錯,我和昔日的我身影重疊。
擠進人山人海的車廂,心竟是難得的平靜。看著人們都在把玩手中的電子玩物,我心中更覺異常的安全。畢竟,好不容易才能擺脫熟人的注意。
車廂一如往常,平穩中帶輕微搖晃,教本已帶睡意的乘客更為昏昏欲睡。有些嘴饞的人,卻不理會廣播的呼籲,繼續進食,令人側目。食物的細碎,像沙子一樣,在人們毫不注意的情況下,悄然掉在地上,再被無意地踏個粉碎。在接著的數個車站,人們再肆意加以踐踏,令碎粉再度粉碎。
到站了,我有意無意地繞過人羣,「不經意」踏中那些有數隻小蟻的食物碎粉。心中,是一陣少有的快意。幕門關上,我回頭望進車廂,想要看看被我蹂躪過的碎粉和小蟻,但列車卻已行駛中。
看不見,罷。
體驗過,就可以了,不需帶走一片雲彩。我毫無留戀,轉身混入人群中,與昔日的我再次分道揚鑣。
回到地面,不自已打了個噴嚏。溫差太大。冰冷的車廂與悶熱的地面形成天壤之別。我沒意欲脫下帽子和口罩,亦不打算更換一些通爽的短袖衫和熱褲。為保自由,我需要將整個人裹得密不透風。相比皮肉上的些許不適,我的精神狀態更值得我投放心思。
生命可以是何其輕巧,也可以是何其沉重。「我」是最高貴的,不容任人宰割;「我」是最卑賤的,可以任人宰割。文化為砧,輿情為刃,物欲為餌。願者上釣,將「我」乖乖奉上。殺,不見血。
皮囊終歸是臭的。吃喝拉撒,離不開物質的束縛。難怪世俗的蟻捨不得離開我的身體。牠們貪婪至極,不停開彊闢土,隨意走於我的皮肉之間。薄得透明的皮膚下,是無定向蠕動著的小黑點。
表面看來,實在嘔心;惟當了解實相後,我只懂為這群小傢伙嗟嘆。自以為掌握世界,闖出一片新天地。真相,不就是牠們的全世界,只是另一隻渺小生物的身體。
宇宙不介懷地球的存在。地球不介懷人類的存在。所以我不再介懷牠們的存在。
恣意掏空我的身體吧。
血肉掏盡,蟻群破體而出。我不支倒地,半伏在這髒臭小巷的垃圾堆中,命不久矣。很高興,我能死得這樣清醒,還能向朝夕相處的蟻群講遺言。
放眼看看外邊的世界,了無邊際的。和長輩們所講的未必一樣。
那不是必然的命運。
你不一定要當蟻后,結婚產子;你不一定要當工蟻,整輩子當奴僕;你不一定要當雄蟻,只能受本能驅使……
我不一定要當媽的乖女兒、男友的結婚對象、無理上司的下屬、社會的小齒輪、舊觀念的服從者……
看!我不就是改變了那所謂的「命運」!若按照舊路走,我這刻該在辦公室裡對著女上司咧嘴笑,哪有了悟真理的快樂?
蟻們,走!去你們真正想去的地方吧。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选集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