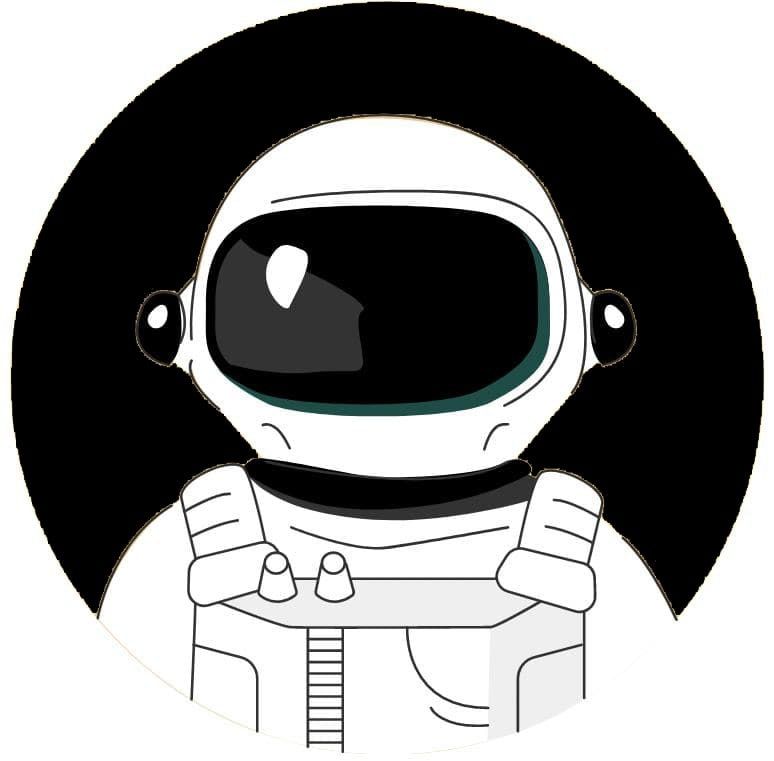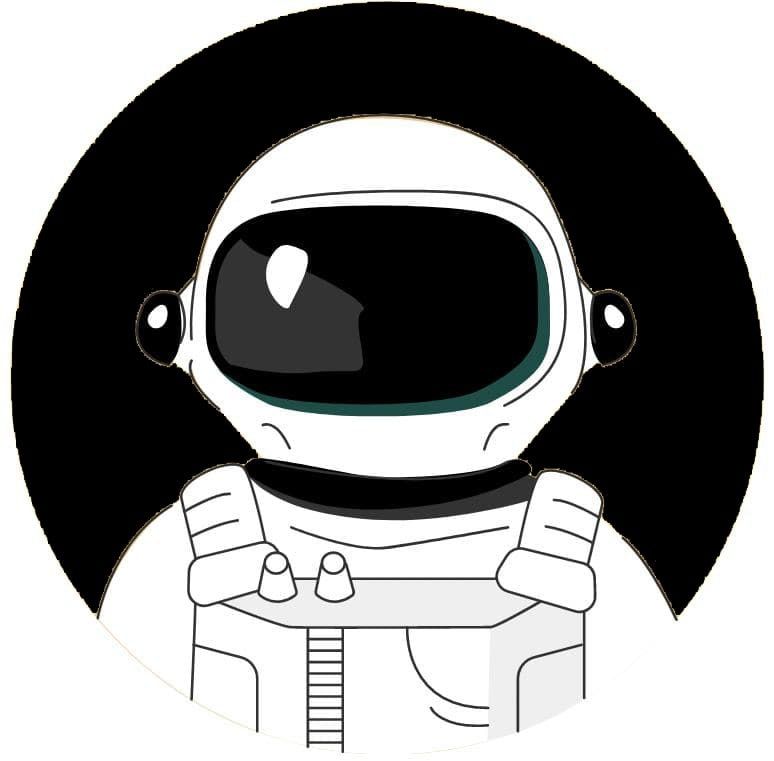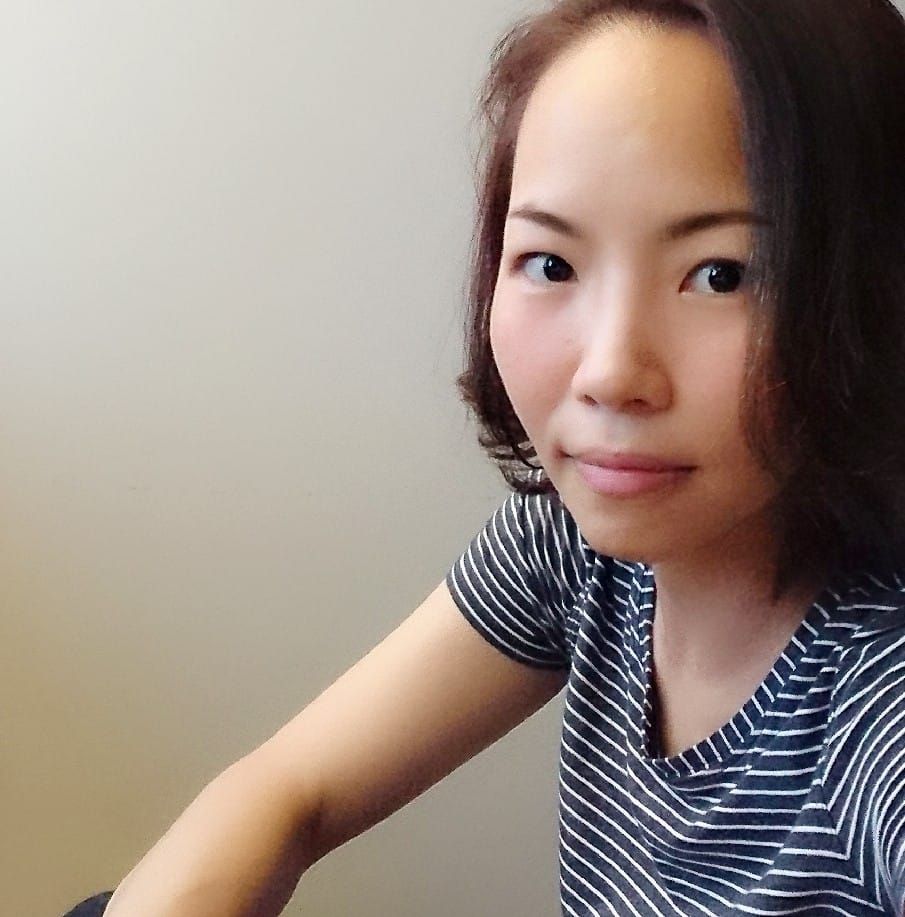緬甸很遠又很近
緬甸與全世界因政變而錯愕與憤怒,但緬甸人以驚人的速度,學習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網路串連與行動技巧,不到100天,緬甸的公民社會意識快速成熟,都市蔓延到鄉村,沛然莫之能禦。
緬甸從長年內戰分裂,走向團結。因為,整個國家成了戰場,不分種族與宗教,支持民主的普通人,都是軍政府追獵目標。
我以繁體中文記錄下緬甸人的抗爭與犧牲,同時卻因台灣疫情警戒封城,我工作的產業完全停擺,而遠走中國發展。
在中國上海,我噤聲了自己,審查了自己,暫停緬甸政變的紀錄,卻每日翻牆閱讀緬甸新聞時,不停地自責。
2023年,緬甸民主抗爭運動潛入地下卻亦發高漲,我也回台重返自由的書寫。

「他們應該被保存下來。」
2015年,我開始緬甸的旅行、書寫、分析與記錄,但我任由文字散落在台港各家網路媒體與專題報導,直到2021年政變。
政變後的100天,每隔3至5日我在Facebook發佈貼文,編寫彙整緬甸當地媒體、自媒體、抗爭組織與外媒報導,直到同年5月前往中國。
「他們應該被好好地保存下來。」邀請我到Matters的友人說。
我安頓了該被記下來的事件,不該被遺忘的抗爭犧牲者,應該被認識的各種抗爭者和抗爭手段。但緬甸,我暫時回不去了。
民主是空氣,一呼一吸是理所當然;即將窒息,就會奮力掙扎。



緬甸選了我
身為一個晚熟的自助旅行者,2013年,36歲那年才開始獨自旅行,首站是寮國。但我也快速跳過青年旅館群聚的外國人,吉他與啤酒,我沒有時間對歐洲人解釋寮國的共產主義背景。
寮國隔壁那塊廣闊的紅色土地-緬甸,難以抵禦的好奇,2014年,我帶著四本書上路:《翁山蘇姬》、《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緬甸逆旅行》《經典緬甸:意想之外的紅土地》。
這是當時台灣市面上僅有的四本與緬甸有關的中文書籍。
第一次到緬甸,我選擇了經典的觀光客路線-仰光、茵萊湖、蒲甘和曼德勒。當時還背大背包、旅行預算只夠搭長途客運的我,傍晚搭上客運,就是長達8至12小時的路途,天亮才下車。
那是一趟很原始的旅行。網路微弱,船伕與車伕幾乎不懂英語,觀光業職員的英語破碎難懂,而我看不懂菜單上的緬文數字,就是我連餐點價格都不知道。
但很純粹。
那四本書介紹的緬甸近代史,尤其是《翁山蘇姬》自傳,與美國記者艾‧ 拉金的《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敘述軍政府極權統治、鎖國時期的民不聊生與民主抗爭,都和我眼前的天然美景,和善純樸的人民-
「這個國家,過去和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是我的第一個疑惑。
旅行在曼德勒郊外實皆山上的寺廟結束。我在階梯上認識了第一個緬甸朋友Earik,「未來,妳能用中文介紹緬甸嗎?」他問。
「或許可以吧。」我沒很沒自信地回答。於是,我們在佛祖面前許了願。
眾神照護,緬甸接納了我這一句緬語數字一二三都講不好的異國人。
我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
2015年的春節假期,我再度進入緬甸。沒打算再去看佛塔,我參考了《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一書,記者艾‧ 拉金尋訪喬治歐威爾故居或警察駐地的路線。
抵達中部大城曼德勒後,我搭上長途客運,前往歐威爾在緬甸最後的居所,小鎮卡薩完整地保存下來的木造房屋,儘管現在的卡薩人全然不識歐威爾。

歐威爾身為殖民警察,卻厭惡母國-英國在殖民地的掠奪與暴力;他熱愛緬甸的東南亞風情與文化,卻同時被當地人和英國人排擠。
這次我多帶了《一九八四》、《動物農莊》與英文版《緬甸歲月》,當時繁體中文世界還不認識,幾乎是歐威爾在緬甸實際生活紀錄的《緬甸歲月》。
仰躺在歐威爾的客廳地板上,他看過的天花板,寫滿了寂寞與憤怒,我哀傷地痛哭了起來。
深走緬甸,就難以迴避喬治歐威爾對極權統治的批判,儘管他沒有活夠久,看到1962年的緬甸第一次軍事政變。
我選了緬甸
超過14年,我的的政治人物幕僚職涯,也在2015年結束。政治和法律的工作背景,我選擇以政治的角度,認識緬甸。
2015年11月,翁山蘇姬與全國民主聯盟,贏得國會大選。
2016年,緬甸成立文人治理的民主政府,急迫地追趕世界的腳步。
尋找喬治歐威爾的路線,讓我從北方卡薩小鎮,縱走直達歐威爾上岸的港口毛淡棉。
我開始對緬甸政府治理邊境省分的「外國人旅行禁令」感到興趣。不論翁山蘇姬是否執政,少數民族武裝組織盤據,內戰與游擊戰頻仍的邊境省分,都是緬甸政府不樂意外國人靠近的區域。
「只有緬甸政府能阻擋我。」2017年,我對阻止我前往邊境的緬甸友人說。在政府資訊不透明的緬甸,一切都是聽聞。
「只能到臘戌,果敢不能去吧。」當我抵達臘戌後。
我在果敢老街的賭場,寫下邊境、博弈產業與賭場荷官的青春哀嘆;同年果敢同盟軍襲擊老街,我再度進入戰後殘破的市區,記錄同樣說中文的果敢族國族認同、流亡與內戰。

許多在台緬甸華人,好奇我如何進入管制嚴密的果敢。「緬甸軍人分不出中華民國護照的『China』是那一個China,戴上觀光簽證,以及緬甸華人沒有區別的東亞臉孔。」我說。
2018年,我自泰緬邊境進入緬甸,那是一個敘事鏈很長的故事,我追逐著吸毒者、戒毒者、協助戒毒者、製毒廠,從罌粟轉種咖啡樹的農家,最後站在一片罌粟花田前。
興奮,和擔心採訪被舉報的恐懼,我站在邊境的山頭,微微地發抖。
緬甸很遠又很近
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前,我還是在2020年3月抵達緬甸北方克欽邦的內陸湖-印多吉湖,一年只有400名觀光客到訪的絕美湖泊。
沒有人知道,一年後的軍事政變,連湖畔的寧靜小鎮隆頓(Lone Ton),都發起抗爭運動。而我,回不了緬甸。
和精通英語的隆頓友人Zaw一起許願,「讓更多外國人來印多吉湖」,「在湖畔開一個有花園的咖啡店」的願望,暫時無法實現,Zaw卻在2021年政變後數月,默默地開掘了他的花園。
我總是在緬甸許願,諸神照看,心很近。
「妳還會再回來印多吉湖吧?」2020年的Zaw問我。
「印多吉湖好遠啊。」「我會回來,我答應你。」
(我希望參加「MattersZine創刊號」,這篇是「個人創作心路歷程」,我選的範疇為「當遠方來到腳下」,此文已選了兩個相關標籤,包括主題標籤「#當遠方來到腳下」、報名標籤「#MattersZine創刊號徵集」,並且在文章底部,貼上我的選集,以作報名活動之用。
在這個選集中,我已選好我的代表作,並排列好次序,整個選集總字數不多於1萬字,選集名為緬甸很遠又很近」。這篇<緬甸很遠又很近>是創作心路歷程,也是「當遠方來到腳下」的第一篇。)
選集連接如下:https://matters.town/@wengwanying/collections/Q29sbGVjdGlvbjoxNTI2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