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處女》:真相、轉型正義與共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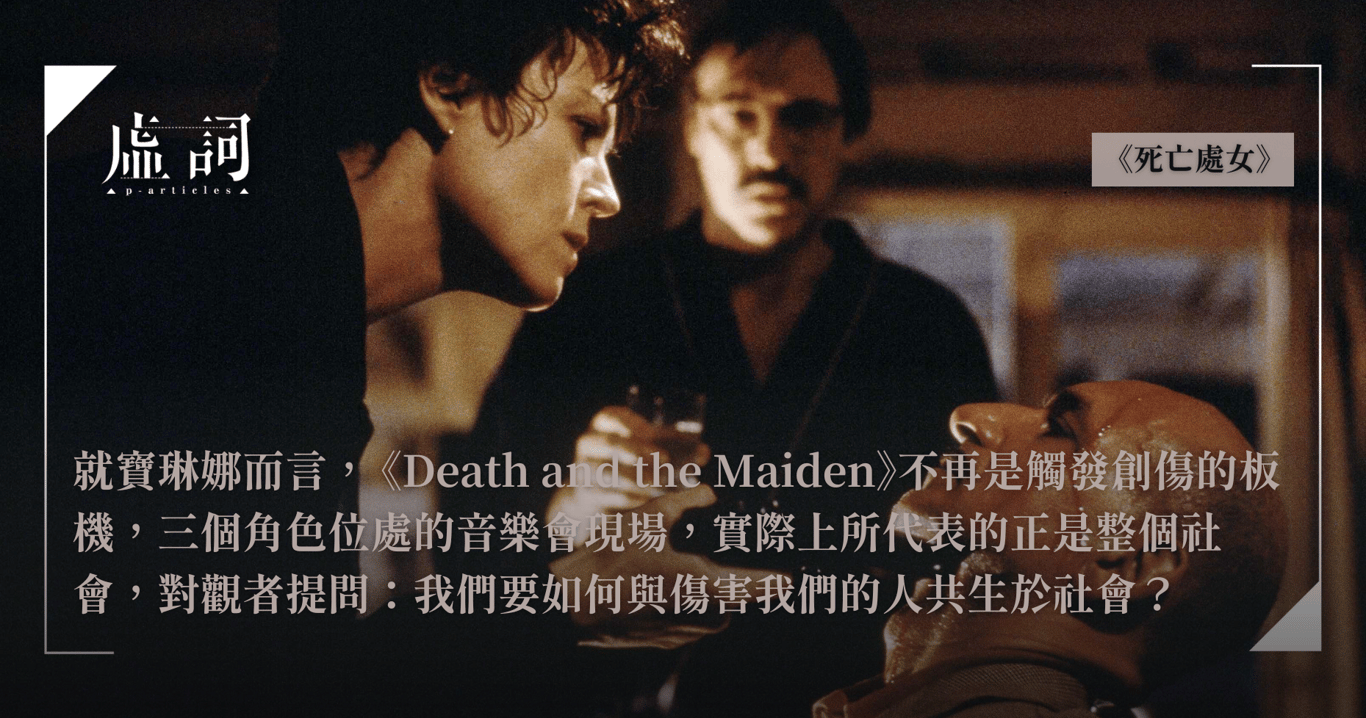
文|曾友俞
舒伯特(Franz Schubert)D小調第14號弦樂四重奏第810號,又稱《死亡處女(Death and the Maiden》。這是米蘭達醫生(Dr. Roberto Miranda)為了減緩寶琳娜(Paulina Escobar)的疼痛所播放給她的舒緩;
「我將根據我的能力與判斷為病人的福祉開立處方,以及永不對任何人造成傷害(I will prescribe regimens for the good of my patients according to my ability and my judgment and never do harm to anyone. )。」而這,是希波克拉底誓言中部分段落(原文為希臘文,本文自英文翻譯)。
然而,在許多當代民主國家的非民主時期,其中不僅有(秘密)警察、公務員、特務是兇手,甚至連我們習以為常預想是司法獨立的裁判官(雖說裁判官也是公務員之一),或必須謹守前述誓言的醫師,卻都可能是這整個龐大犯罪結構—組織—的其中環節。例如有「死亡天使」之稱的門格勒(Josef Mengele)就是著名的例子。
九零年代是杭亭頓(S. Huntington)所說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參考曾友俞,〈民主提供選擇,主權歸於人民──讀《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 ),所謂的民主化係指「從非民主到民主的過程」。在客觀國際的層面上,民主化是在柏林圍牆倒下、蘇聯垮台的情勢下出現;在主觀國家的層面上,民主化則引起了一個當代的問題:轉型正義(Transisitonal Justice)。
轉型正義在各國有不同的實踐,例如波蘭的除垢法案、南非的和解途徑或是我國的不當黨產處置措施等等。姑且不論各種制度實施的良劣,重點在於這些制度的創造與實踐,都是為了處理非民主——威權時期的國家不義行為。
「不義(Unjustice)」,而非不法(unlawful),正是因為實證法(Positive law)與自然法(Natural law)是不同的規範,甚至原先作為實證法學者的賴特布魯赫(Gustav Radbruch)在二戰後也改變了立場,進而提出了著名的賴特布魯赫公式:「實定法具有優先性,除非,實證法違反正義達到令人難以忍受的程度,將以正義作為終極判準。」
回到《死》的故事,米蘭達醫生之所以有機會播放舒伯特的音樂給寶琳娜聽,正因為他是被國家機構聘任去確保犯人即便受到虐待、拷打,也能在有專業人員的看顧下維持生命的專業人士。如果米蘭達醫生只是這樣,或許他還有機會可以用艾希曼(Adolf Eichmann)式的語言辯解(參考曾友俞,〈讀《平凡的邪惡》──鋪在絞刑架之路上的是名為運氣的紅毯〉 )。但是,實際卻比此更加醜陋。
故事中並沒有揭露具體發生的國家為何,然而,這恰巧映襯電影在九零年代上映的時代背景。亦即,這可以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故事,因為任何一個第三波民主國家都有與這個故事大同小異的歷史,那麼也就或許會有一個、無數個這樣可怕的故事。
風雨中汽車爆胎的吉拉多(Gerardo Escobar)被好心路人給搭救,一趟車程載送回家,但妻子寶琳娜卻神經兮兮地躲在屋內,連聲招呼也沒有打。吉拉多向這名好心路人自我介紹是名律師,這位路人在回程路上聽到廣播揭露吉拉多即將擔任國家委員會的主席時,滿心歡喜地在深夜再度來訪希望表達自己的欽佩與欣賞。寶琳娜卻拿起了槍,躲在陰暗的臥房,伺機爬窗出外,開走了這位路人的汽車,搞得吉拉多尷尬地必須向這位路人致歉,愧疚於其善心卻遭妻子糟蹋,然卻也因此良機使得二人有機會小酌相識至醉方休。
若非具後見之明,作為觀眾的我們肯定是一頭霧水。除了寶琳娜不只不接待賓客,甚至開走客人的車,更別說拿走家裡所有的錢,她的歸來甚至不帶給餘下二人慶幸,卻是嗅聞這位客人的味道後,拿槍柄敲破他的頭,在其暈厥時將其綁縛,在吉拉多醒來後寶琳娜再向其指稱這位客人正是先前虐待、拷打,甚至強姦她的醫生,米蘭達。
妳瘋了。
這是正常人再正常不過的反應。對於自己陳述的經驗也有提到是在眼睛被矇著的寶琳娜,唯一的憑據僅有自身的「經驗」,然而對於從事法律專業的吉拉多而言,這些個人主觀經驗絲毫一點都不具有證據的適格性。退一步來說,縱使這些陳述足以稱作證據,如此的訊問方式也毫不符合國家在民主化過程必須努力實踐的「法治(rule of law)」原則,其中包含了被告為自身辯解的權利。更不用說,即將成為國家委員會主席的吉拉多,是沒有可能會接受這樣的做法。
寶琳娜的依據——聲音、味道以外的,最重要的是米蘭達的車上找到了關鍵:一卷舒伯特《Death and the Maiden》的錄音帶。而這也是她把車給開走的理由。但對於「法律」而言,這足夠嗎?難道一個好心的路人不能正好有欣賞舒伯特音樂的嗜好?以一般的觀點而言,已經過於薄弱,從法律的觀點來說,更不可能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
然而,從寶琳娜的生命經驗而言,她是不可能忘記這組旋律的,這是一組她必須躺在自己排泄物上,受到被電棒放入陰道的虐待,以為將遇到救贖,卻是再一次一次共十四次強姦她將其推進更深地獄後的制約。這組旋律、這些味道、這個特定的聲帶震動,就如同帕夫洛夫的鈴鐺一樣勾起寶琳娜的創傷,而這些跡象也是讓她得以辨識出犯人為何的根據。
相對於此異常,吉拉多的律師身分所代表的正是一種秩序(order)——正常(ordinary),更別說他不只是進入民主時期要擔任要職的人物,在故事中的更早時期中他也正是威權時代的反抗者。於是他詰問道:如果我們反抗的是這樣的強權,我們能否容許自身以這樣的方式對待他人?尤其,若要以法律原則來討論,也無從迴避無罪推定這個大大大原則。
這裡吉拉多所提出的問題,類似於倫理學中的經典:我們能否接受對於恐怖份子的拷問進而得出炸彈位置以避免多數人的傷亡?在義務論與功利主義的不同立場會分別得出不同的結果,一者是行為的道德性不取決於其後果,而是依照行為本身而定;另一方則是認為行為的道德性以其後果的利弊多寡而定。但是,寶琳娜對於米蘭達的拷問——或說逼供,畢竟沒有虐待—僅是限制人身自由並以生命威脅,卻是為了求取「真相(Truth)」,她要聽到米蘭達醫生的自白(confession,或稱告解)。
真相的獲得並沒有任何的利弊可言,多了真相對於寶琳娜而言並不會增加任何利益、減少弊害,寶琳娜就如同許多民主化社會所處理的轉型正義議題一般,亦即,真相的追尋並非為了任何實際的利益,卻只因為真相本身所具有道德重量而如此汲汲營營。於是,這個道德疑難就不再是不同倫理學立場之間的衝突,卻是義務論中的不道德行為之間的衝突—不誠實與傷害他人此二行為間的衝突。問題會再衍生到是否能以傷害他人的方式強迫他人誠實?手段既然不能正當目的,面對他人的不誠實我們能否同樣以不道德(卻不是同類型的不道德行為)的方式對待之?但若他人的不道德行為(欺瞞,甚至是對自身傷害該人此同屬不道德行為的欺瞞)是另一人不道德行為(傷害他人)的原因時呢(亦即二者間具有因果關係)?
這些問題在電影中並沒有解答,甚至這些也不是電影所直接提出的問題,惟《死》的故事即便沒有就這些問題進行處理,卻提出不同於這些問題所位處的道德層次的另一個層次的解答:政治上的解答。
南非在處理轉型正義的問題的特出之處,正是在於其以「真相換取特赦」的模式實踐。藉此,真相得以見光,社會才能和解前進。「寬恕與和解不是假裝沒事,對事實視而不見;不是相互拍肩搭背,對錯誤視而不見。真正的和解會掀開令人厭惡的一面:虐待,痛苦,墮落和真相。有時它甚至讓情況惡化。要實現真正的和解,就得冒險。但終究是值得的,因為面對真相才得以撫平創傷。虛假的和解只能帶來虛假的復原。」(Desmond Tutu,《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頁353)
吉拉多原先固然對於如此瘋狂的行徑難以信任,甚至對於寶琳娜曾受過創傷進而評價其陳述不可信——也就是 Miranda Fricker 所說的證言不正義(testimonial injustice),但隨著寶琳娜指出更多當初虐待她的人的特徵,例如會引用尼采的語句這個特點,也正好是寶琳娜竊車離去時米蘭達與吉拉多談話時曾說到:「你知道尼采說什麼嗎?我想那應該是尼采,嗯,我一直說那是尼采,不論誰說的:『我們永遠無法完全擁有女性的靈魂。』」以及寶琳娜令吉拉多擔任米蘭達的「辯護人」以滿足正當法律程序的需求前,其以不同的故事版本(虛假版本)傳達給吉拉多,經由吉拉多自身轉達給米蘭達後,米蘭達卻說出了真實的故事版本。如此種種,才讓吉拉多願意相信寶琳娜。
當然故事最後仍有轉折,吉拉多去電市政府確認在那段寶琳娜聲稱遭到不當對待的時期取得了米蘭達的不在場證明,然而卻也正是吉拉多親口告訴寶琳娜在民主過渡的階段許多證據都可能被捏造、湮滅。寶琳娜的條件是若米蘭達吐實,就會讓他走,但對於被綁架的米蘭達來說當然無法安保己身,在一再否認自身犯行同時有時間壓力的情形下(因吉拉多受到生命威脅,國家安派維安人員將於清晨抵達),寶琳娜將米蘭達帶到岸邊,那個她將汽車墜入海中製造事故現場的岸邊,跪地與米蘭達同高,兩眼直對著另一個人的兩眼。
「看著我,現在看得清楚我嗎?你不認識我嗎?你沒告訴我你骯髒的想法嗎?你沒有告訴我你的秘密嗎?你沒有強姦我嗎?你沒有把你的陰莖放在我身體裡嗎?幾次?」
「有,有,許多次,我強姦過你很多次,十四次。」
「你放音樂。」
「對,我放音樂因為我想安撫你。我一開始很擅長,花了幾個星期,我很強壯,我奮力奮鬥,沒人像我如此這樣。我是最後一個,最後一個品嘗的。沒有人死掉,我發誓,我救了好多人,我讓他們好過多了。這就是如何開始的,是我如何捲入的,他們需要醫生,我哥哥是秘密警察,他告訴我需要有人確保沒有人死亡。我清潔過你了,你都是汗,你告訴我:『我很髒』,而我把你洗乾淨了。其他人慫恿我,『快啦,醫生你不會想要錯過免費餐點吧?』我就頭腦不清了。而我心裡也覺得自己開始喜歡了,他們把人丟出來,把人綁在開燈的桌上,你不知道那些房屋很亮,人們無助地躺在那,而我也不必當好人了,我不用誘惑他們,我理解到我不用去照顧他們,我有所有的權力(I had all the power),我可以摧毀任何人,我可以讓他們做我想他們做或說的。我迷失了,我變得好奇,病態的好奇,這個女人可以承受多少?她的陰道會變怎樣?電擊的話會乾掉嗎?之後可以高潮嗎?我喜歡裸體,我會慢慢脫掉衣服,讓褲子掉下,所以你可以聽到我在幹嘛,我喜歡你知道我將要做什麼,我在明亮光線下裸體,而你看不到我,你不能叫我做什麼,我擁有你,我擁有所有人,我愛這樣,我可以傷害你也可以幹你,而你不能叫我不要,你還必須感謝我。我,我喜歡這樣,我很遺憾這結束了,我非常遺憾這結束了。」
道出事實、罪行的米蘭達並沒有得到任何制裁,懲罰與否是另一個哲學問題。寶琳娜只是如同她所承諾的,得到真相就讓米蘭達離開。米蘭達這個角色固然也可以探討權力與性、與腐化或者個人因創傷所致的人格扭曲,但我想《死》的故事更重要的議題是:在一個社會中罪犯與被害人如何共存?
故事的結尾在一場音樂會上,演奏著《Death and the Maiden》,平面席位上坐著寶琳娜,她看向二樓的席位,那裡坐著米蘭達。米蘭達再回看平面席位,望上二樓的則是吉拉多。就寶琳娜而言,這首樂曲不再是觸發創傷的板機,畫面所呈現的三個角色位處的音樂會現場,實際上所代表的正是整個社會。這個電影對於觀者的提問即係:我們要如何與傷害我們的人一起聆聽音樂?或說,我們要如何與傷害我們的人共生於社會?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