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评书 |《花冠病毒》——毕淑敏
这本书并不难读,但却花去了我十多天的时间,也许我错了,这本书其实真的很难读。
掩卷遐思,觉得这是本很有趣的书。读书的时候,人在书里,顺着叙述一直走,恍惚间进入了过去一个平行、自己曾深谙的世界,那个世界里人们的一举一动我都无比明了。闭卷之时,又不得不注意到自己面前这个真正的世界,一个不太需要集体主义、不会有压迫下的牺牲、传颂,一个关注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脸孔,而非千人一面,这个世界希望在反思里朝着文明再进一步。这两个世界彼此是那么遥远,却让一个现今肆虐的“新冠病毒肺炎”拉得仿佛近在眼前。
“花冠病毒”源自于显微镜下的SARS病毒,形状似美丽的花冠。作者毕淑敏把当时深入SARS疫区的经历写出来,“魔幻现实”成现在这般模样。读罢,有两个价值让我觉得值得探讨。
「一」社会及文化价值
- 「官场现形记」
这些“怪现状”在《花冠病毒》里并没有被审查,也许是被审查了,但是没有完全不谈。相反,领导对于撒谎、为什么要撒谎、撒谎分真假好坏等等都有详细描述。不论是在疫情瞒报还是承担责任上,撒谎及为撒谎寻找冠冕的理由在任一当官的眼里都是能一笔带过的,甚至能再添一个“为人民”、“为你们好”的用心。
疫情数字瞒报时的撒谎是为了免去恐慌,但缺失真相的人民在黑暗里不会更怕、更恐惧?再者,瞒报与扯谎里藏着的是对大众判断能力的不屑。以“父母”的姿态对众多成年人行管理小孩子的方法,更不用讲这样的办法对小孩子都被证明并非有效、并不健康的。

“院长们面色凝重。……撒这样的弥天大谎,……每个人心里都惶恐不安饱受谴责。”
在书开篇二、三页处,作者便道出了几近荒诞的“花冠病毒处理现实”:
“技术性处理”、“瞒报”、“缩小死亡数目”……那些书里得以先戴头盔的人这么怕我们恐慌?一旦“恐慌,悲观情绪蔓延”,人们进入失望情绪,是不是则无法控制了?我质疑,一定也有很多人质疑。不过,有一个是没有错的,失望这一情绪太难忍受了,似乎已经到了无法设想的地步。
但是很多人不明白,「失望」是自己与自己的较量。
2. 「内与外」
书里有个人——郝辙。这个人偷了病毒毒株,买到YY(字母代替)去了。女主人公罗纬芝及所有的视角都将他视为“叛徒”。作者对郝辙的描写也着重于他与女主人公几乎发生的Casual Sex而带着无限的蔑视。交易完成,郝辙从海外致电罗纬芝,几近流氓式的描述包罗了他为了洋车、洋房干的出卖“大家”的不齿行为,并最终道出“科学是有界限的”这一狭隘概念。
这些桥段的社会价值在于成书的2011年及现今这样的思维方式并未有一丝改变,而这样极端的科学理念似乎多少背负着建政之初的“令箭”,而并未有些许“打开”、“开放”的念头。现今新冠肺炎疫情时出现的很多反应均是能在书里找到对应之处的。那这究竟是该我们欣慰还是担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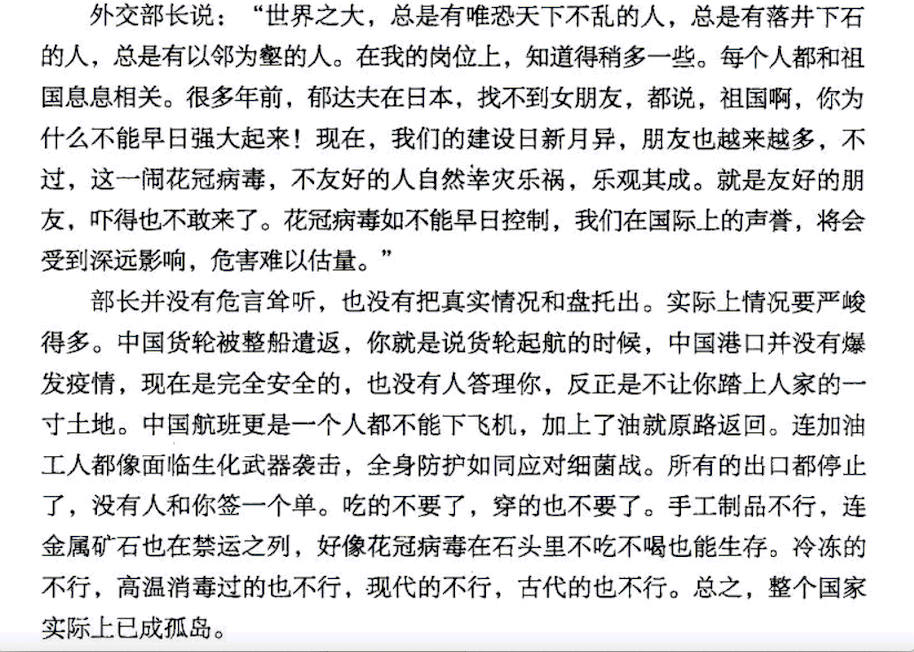
3. 男女的平等(仇女?)
这一层既有社会价值,也有文化价值。在《花冠病毒》这本书里到处充斥着对于女性外貌、价值、年龄的歧视、自我歧视/贬低。
罗纬芝是作为一个大龄剩女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作者很直接地指出相貌并不出众的罗纬芝婚嫁的机会十分渺茫。“大龄”、“没人要”、“剩女”这些具有歧视色彩的标签反复出现,自然成了一个没有什么不当的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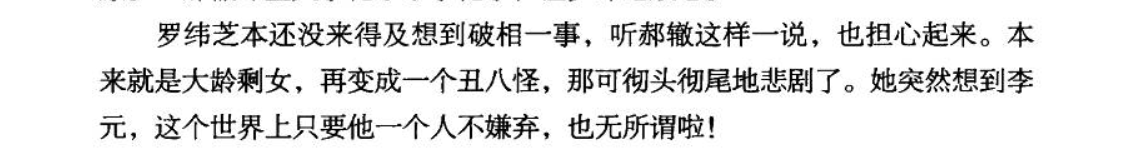
有意思的是,作者自己是女性,而作为女性,似乎也缺少了自我审视与尊重。
本书出版了近十年,这些标签并未有一丝改观。对于“性”、“处女”的解读也在书里形成了一个极有趣的社会缩微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标签与观念?它们为什么萦绕不散?
罗纬芝与李元是本书仅有的爱情线。而罗纬芝处处重复着自己的期许,希望“有人要”等等。作为受过教育的女性,“罗纬芝们”实在令人怜惜又愤恨。
书里市长孙子得了“花冠病毒”。作为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作者费了不少笔墨。写到为了孩子放弃工作待在家母乳的儿媳苏雅,身为女性的作者竟然用了“奶牛”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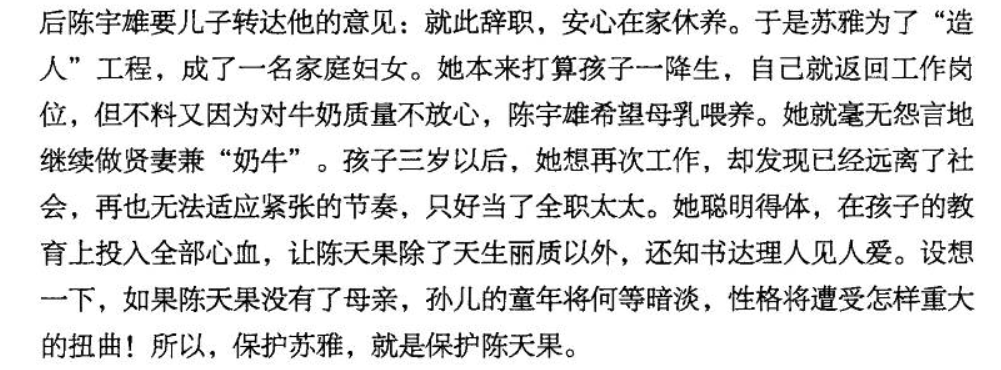
而在苏雅也得了花冠病毒肺炎从而需要罗纬芝带有抗体的血清救助时,罗纬芝的想法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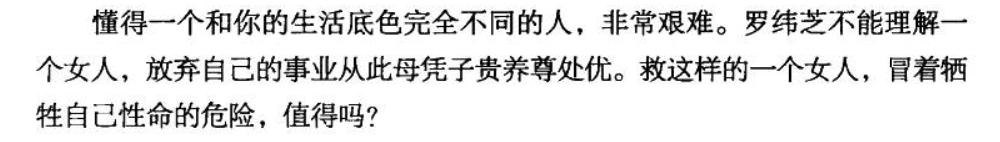
我认为,这是本书最为震慑人心之处之一。一个人该不该被救助竟激起“有能力救助者”罗纬芝心里这样的想法。读至此处,我似乎无法表达,而究竟该怎样表达,怎样反击这样的思维方式?似乎很难解释清楚。
读毕,了解这是三次修改的成书,还是留有此类并不是从人道主义观出发的思考,着实痛心疾首,难掩失望与无助的情绪。但是,这也是本书的社会及文化价值所在。它所体现的正是过去二三十年里经济发展下掩盖的人性及平等价值观的缺失;人们在荒漠里摸爬滚打。这正是世界所需要了解的社会价值:痛且真切。
「二」文学价值
《花冠病毒》一书的文学价值远不及其社会文化价值。在我看来,它的文学价值基本相当于零。即便作者是作协的作家,但她的文笔几乎差到无法体验到一丝审美。行文充斥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也一定是作者能精炼背诵的文本节选,从“星星之火,燎原之势”到郝辙与境外“某股势力有所联系,所以他力排众议到抗疫第一线去,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等,很多都是平日里依旧能看到、读到的判断。
在此,我愿从书里所用的一些不当比拟里举例——
- 不当比拟
“李元的身体像一株十一月的白桦。”白桦的笔直在那个时代都是被传颂的,当然也是被背诵的。“身体”比作“白桦”,还是“一株”,算是作者描写手法的贫乏。更多是刻板性的比拟,正直的人一定是白桦,而反面人物呢?
2. 纳粹军官
以“凤凰男”郝辙比纳粹军官,罗纬芝比犹太女人是在二人自愿未果的Casual Sex Scene里。太不当了!(115页)
当郝辙让罗纬芝宽衣解带的时候,他则在作者眼里成了“纳粹军官”?这样的比拟显示了作者对于纳粹/犹太大屠杀的不了解,也极具侵犯性。一个男人,即便是书里定性的“叛徒”,在令女人宽衣时便成了纳粹?自愿宽衣的罗纬芝便是受虐的犹太女人?这样的比拟在太多层面都错了,而这样的比拟至今都在网上、宣传机构里层出不穷,这些是很严肃的错处,是教育的失败处之一。
3. 残疾人/生病的人
155页处,作者把眼睛在恐惧时睁大比作与“得了甲亢”一样。这似乎失去了对于甲亢病人的尊重。Susan Sontag在1978年写的Illness as Metaphor正是希望通过对病人及其症状带来的歧视、隐晦意义的反思而让生病的人有一个不偏颇的社会环境来康复。而书里这样的比拟,眼睛睁得大,与得了甲亢的一样;什么样,又会与盲人联系起来……在这本抗击“花冠病毒”的书里,我没有看到一丝对于病人的关爱,反而,充斥着等级观念——市长孙子生病了不得了;毒株卖到海外不得了;普通人连最基本的数字、消息都无权获悉。这样的康复,太难了。
4. 对于萨特(Sartre)的理解
首先,作者是这样描述全球化的——“全球化时代,地球是扁平的,没有什么东西能真正将人们……”在这里,我认为“扁平”二字是不当的。地球并不是扁平的,而将地球认为是“扁平的”至今仍是一些阴谋论者的看法。虽然作者并不是要重复这一阴谋论,但是,扁平的地球是不太好的比拟。
在文学批评里,“扁平”二字其实有它自己的用法。它是与“立体人物”相对的“扁平人物”,是类型化人物,没有真正为人的立体性,更多的是单方面个性。关于莎士比亚及其他作家的代表性扁平人物在网上有太多文章,多是互相抄袭。“扁平”这个描述并不准,也没有什么深度。将愈发“全球化”的地球这样描绘,称为“扁平”是不对的。相反,全球化带来的是多元化,多元化的人、多元的文化都与“立体”相联系,正是扁平的反面。
其次,接下来作者讲萨特的他人是地狱理解“不仅过时,而且根本行不通。”这与之前的全球化、地球“扁平”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是很混杂的思维构建。更进一步的是,萨特关于“他人是地狱”的理解也可以看作是在人与人之间相互过度依赖、互为拖累下提出的概念。萨特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恶性循环,存在的恶性联系,无法自拔,无处逃遁。全球化,人与人联系更紧密,那萨特的理念究竟是过时、行不通还是……?
再者,作为存在主义,萨特讨论的是philosophy,是人性,是人类自天地混沌之初便有的思考,会“过时”、“行不通”?我觉得此处不应是一个作者应该犯的错。
5. 最美的比拟
赘述过多都是不好的地方。《花冠病毒》还是有写得很美好的比拟。下面是我认为写得最好,也最能代表全书的一处。
得花冠病毒的人们纷纷死去,已经无法及时焚化,所以当权者找到了一处常年贮存红酒的地方,征用了。红酒腾出来,尸体移入,低温储存。藏酒的老板道出了他的神伤,“这里永远不能再藏酒了。……陈年的葡萄酒是有灵魂的……”而谢耕农道,
“这里将不缺灵魂。”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