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喬治·桑德斯〈小強〉
快樂似乎是一種無法被填滿的欲望,使得我們在滿足的同時不滿,在得到的同時匱乏,我們在滑手機的時候既愉悅又焦躁,這種矛盾,或許是因為我們錯估了生命的基底。
淺談《勸誘之邦》
輝安劑很靈,每次鏈接都能讓心情好轉,只不過,不久後,我發現,一天鏈接八、九次的人,時時刻刻好快樂,可惜那種快樂,像嚼錫箔紙。一旦,為了追求那種快樂而生活,一個人即便非常非常快樂,都樂島快哭了,不久後,照樣會覺得,不夠快樂。
談卡夫卡《城堡》
作為外鄉人,K始終面臨相似困境,所有他所以為的簡簡單單的事情,在村中人看來都是極其困難,又極其難以解答的,而那些村中人拋出的答案,也是人言人殊,充滿了矛盾,至此即便讀到最後,讀者仍與翻開小說前的狀態差不多,幾乎無法說自己知道任何事情。
閒聊愛倫坡
隨意談一下愛倫坡
誰是你靈魂的擺渡人?
人死後會去哪個世界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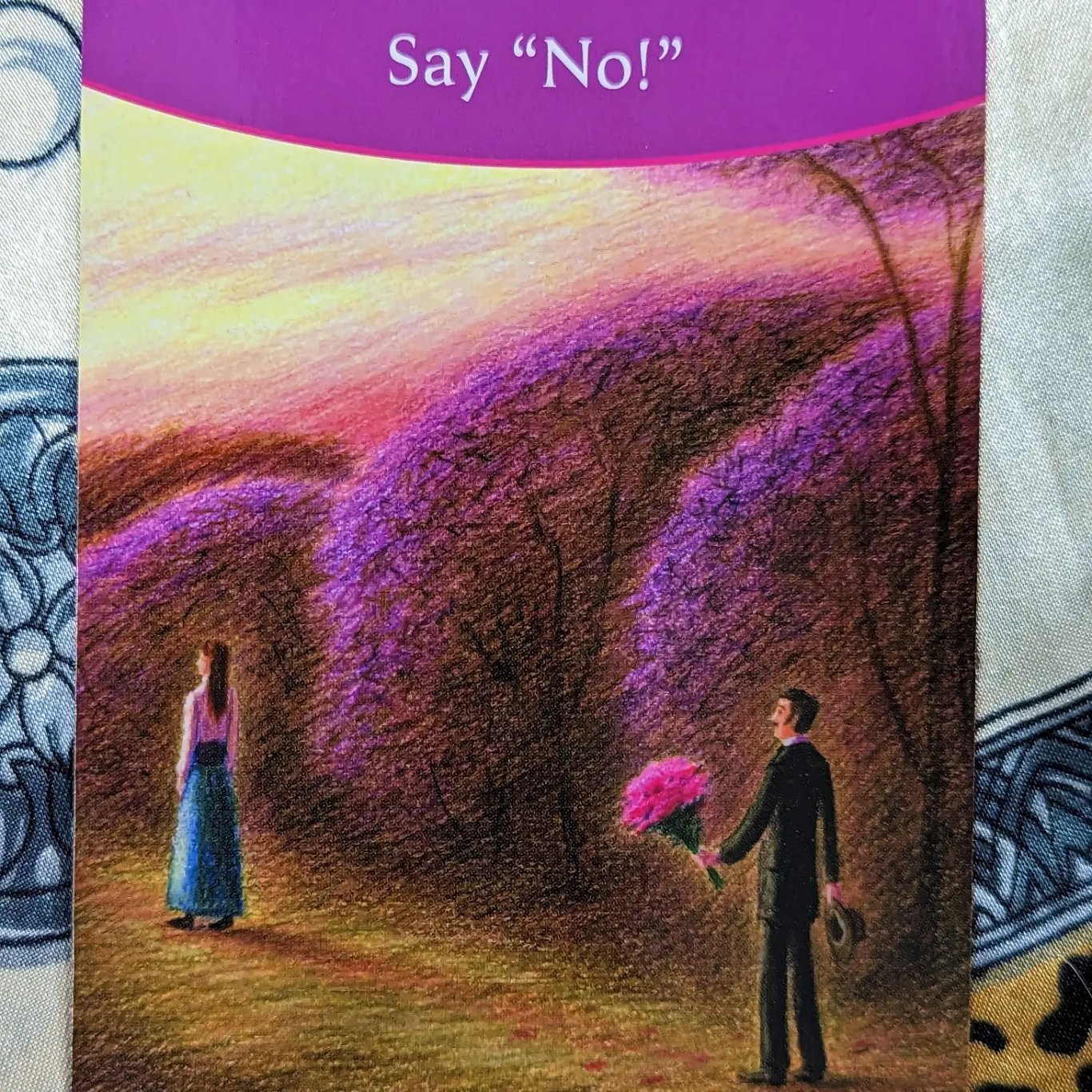
談哈娜‧貝爾芙茨《被消失的貼文》
如果影片出現某人把貓扔出窗外的畫面,那只有並非出於殘暴動機的情況下才可以保留;不過,把貓扔出窗外的照片卻是絕對沒問題的。人在床上接吻的影片也是允許的,只要我們不會看到生殖器或女性的乳頭,而男人露乳頭則毫無問題。
談約翰·史坦貝克《憤怒的葡萄》
小說故事開始於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當時因黑色風暴事件與經濟大蕭條的夾擊,大批來自德克薩斯州和奧克拉荷馬州的農民被迫遷徙至西部尋找生機。整本書正是以約德一家的視角,帶領讀者去走過這段遷徙之旅(上半部)以及在加州遇到的種種苦難(下半部),同時穿插著「去個人化」視角,以更為抽象的「...
談韓炳哲《倦怠社會》
憂鬱的人會抱怨:「沒有什麼是可能的。」但這種情形只有在一個相信「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社會才可能出現。
談波赫士《小徑分岔的花園》
我心想,一個人可以成為別人的仇敵,成為別人一個時期的仇敵,但不能成為一個地區、螢火蟲、字句、花園、水流和風的仇敵。
《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論點修正
在我眼裡,這個題目彷彿是夢境的畫面,輪廓模糊,可是真實性不容置疑。圖書館裡,學生在努力啃書,肥胖的館員兜著一個查圖書目錄的女孩打轉,我的論文題目甚至比這些人都來得真實。我心領神會,那是一種不待言語的知性。
談安妮·艾諾《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
我的人生,也許只有唯一一個真正的目標:將我的身體、感覺、想法轉化為文字,也就是某種清楚易懂、普遍性的東西,好讓我的生命完完全全融進其他人的腦海和生活。
讀《棺材告白者》~ 有些遺願不會默默進墳墓
遺願就像指紋,揭露了一個人最在乎什麼。你是否會僱人出席自己的葬禮,向眾人說出祕密?那可能是你一生中最在乎的價值,也極可能是救贖與生命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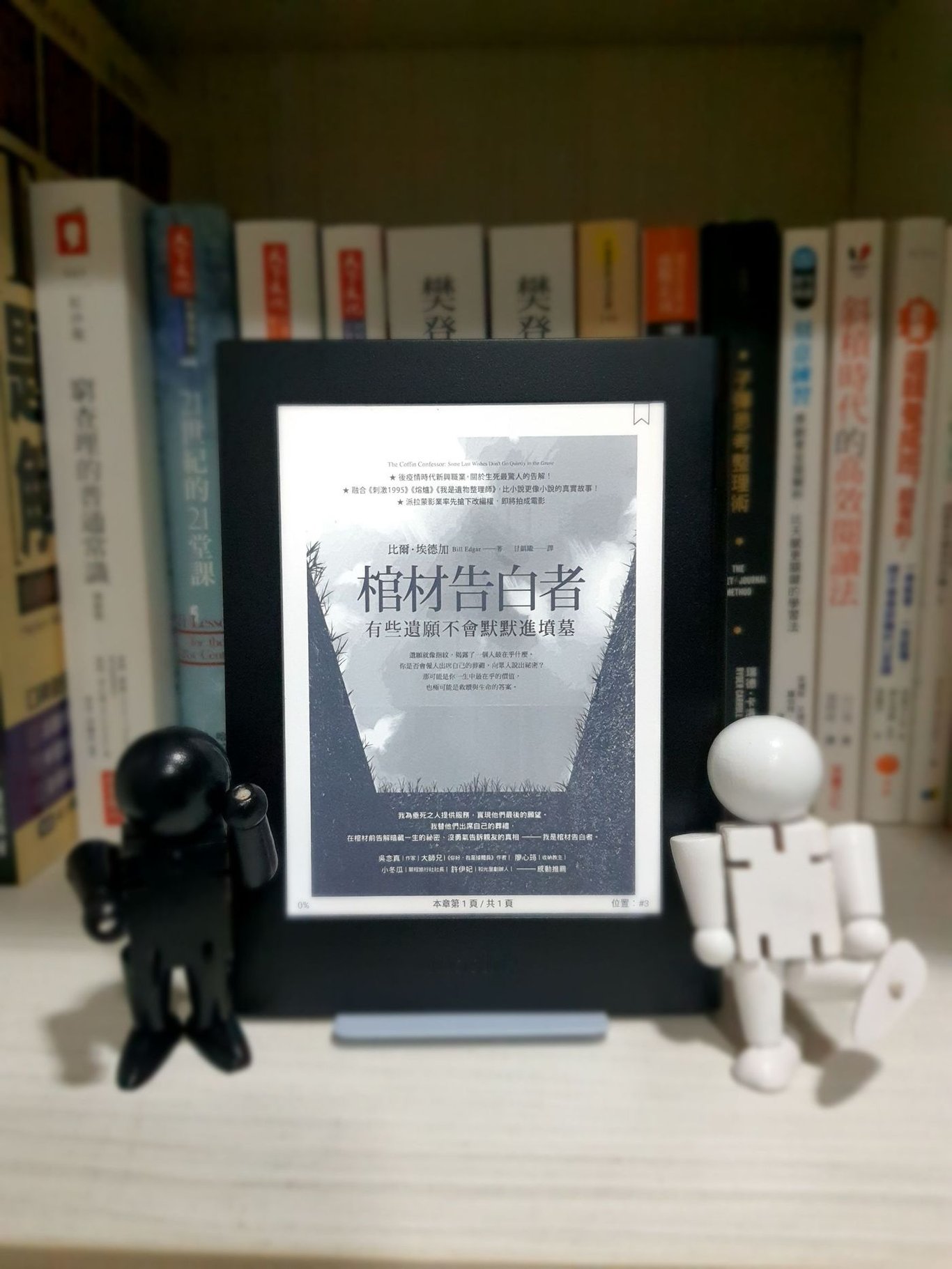
關於純文學定義的一些想法
他認為給語言下一個定義是不可能的,而且那樣的思維會遮掩語言和意義如何運作。語言有無數不同的使用方式,為了了解語言是什麼,我們必須研究語言如何運作,而我們只能透過研究語言實際使用的例子來理解。
《俄狄浦斯王》读后记
生命是无常的,没到最后一刻,你都不能说一个人活得幸福。

談《網路讓我們變笨?》
如果我們瀏覽網頁的時間多過閱讀書籍的時間、互相傳遞簡短文字訊息的時間多過寫出完整章句的時間、在網路超連結裡跳來跳去的時間多過寧靜沉思的時間,這些舊有的心智功能和思想追求就會變得脆弱,並且開始瓦解。
讀《不便利的便利店》
神秘的大夜班店員 - 獨孤,默默地為城市裡失意、傷心、喪志的人們,在不便利的便利店裡加值,為人生路途上找到些希望的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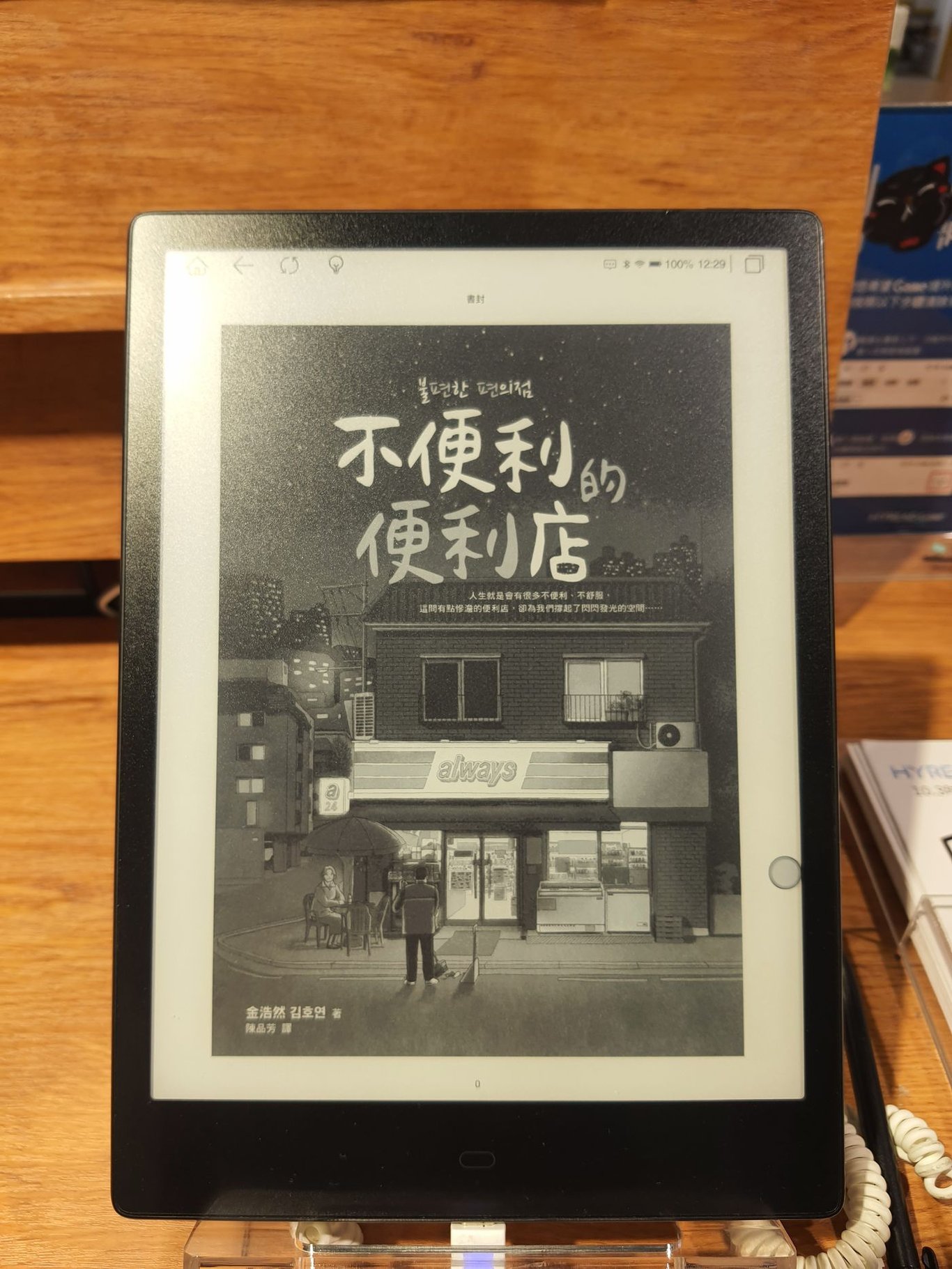
談艾莉絲·孟若〈蕁麻〉
未來的缺席我能接受,但那只是因為我還不明白缺席的真正涵義,直到邁克不再出現。我生命的領土將如何改觀,像歷經了一場山崩,所有意義隨著土石流被剝除,只剩下失去邁克這件事。
談談卡爾維諾《女泳客奇遇記》和《汽車駕駛奇遇記》
只要我們打電話找不到人回應,我們三個就會繼續沿著白色的車道標線來來回回,不再有起點或終點為我們單純的奔波往返附加各種感受和意義終於擺脫了人和聲音和心情的笨重厚度,簡約為發光的信號。想讓自己與所說的話等而同之、不再因為我們或其他人出現帶來雜音導致話語扭曲變形,那是唯一方法。
談卡佛的《大教堂》
都是沒什麼營養的筆記,不建議讀。
淺談班雅明《說故事的人——論尼古拉·列斯克夫的作品》
說故事者從死亡那裡借來權威,而他們所能敘述的一切也都已經過死亡的核可。換言之,他們都知道,應該讓自己所敘述的故事重新回到大自然的演變過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