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戴锁铐的娜拉:徐州八孩女子与农村父权叙事
徐州丰县女子在寒风中带着锁铐木然站立的场景令人痛心。距离鲁迅发表那篇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已临近百年,距离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宣言已经70年有余,占人口一半的女性的社会处境近年愈发获得公共关注,因而这一事件的后续发展尤其让人愤怒。(截止22日在Matters发稿,江苏省政府成立的调查组并无回音,网传地方政府反而进一步在“维稳”方面开展工作。)
本文意图探讨并批判一种并不主流但值得回应的话语,即一种站在农村男性的立场上为其作辩护的话语。这种话语宣称,像董某那样的农村底层男性是社会发展不均衡下的弱势群体,因而买女为“妻”(以及后续的罪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甚至暗示这是一种对农村的补偿。它不主流是因为拐卖事件基本能够达成公众的道德共识,但它又值得回应,是因为这种贬低女性的论调屡次在农村与女性议题相交的场域里复现(如农村高彩礼问题)。
我们完全应该看到,城乡二元结构很重要,城市化发展主义所导致的政治经济不平等、特别是对农村的剥削也很重要,它们在过去几十年中形塑了人口流动及其性别分布的基本形态。然而,这一前提这恰恰是批判性地理解农村各种问题(包括性别问题)的起点,而非辩护词。
在我们所看到的拐卖所牵连的社会关系中,为男权秩序服务的人贩子和农村男性买家仍然能够以极端的方式(包括连骗带拐)压迫和剥削女性,再借助地方宗族势力、婚姻制度的合法化功能、家庭作为“家务事”的私人领域话语、对基层政权的影响力等限制女性的自由和自主。在这里,男权秩序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也要把当下更复杂的经济性安排(如财产分配)包括进来。另外,与阶级、民族/族群相关的不平等及其交叉性(intersection,意指社会系统的多个等级化维度在个体处境的交汇)也从中浮现(参见:“小花梅”背后的怒江傈僳族女人:被讨走?被拐卖?还是自主婚姻迁移?| 访谈)。
如果拐卖女性是对农村利益的“无奈”补偿,那么这个农村指的究竟是谁的农村?所谓“农村利益”的主体,不包括女性、只有男性吗?亦或者,是假借农村男性名义、却从这种野蛮关系(如果按照它的同情者所说,即对所谓农村底层男性群体的收买)获得好处的既得利益群体?
这种将女性排除出去的农村(男性/父权)叙事,甚至也为一些怯谈“性别”的农村研究专家所共享。但如此一来,这一男性化的“农村”视角最多只能作用于当下城乡结构性关系的维系,实际上无法改变农村男性在这一政治经济系统下的困境,乃至助长城市话语对农村的道德化优势(后者被简单地建构为落后、愚昧、未开化的前现代空间,农村男性则被认为是与暴力、犯罪同义的非人危险形象)。另一方面,它也将破坏或消解国家的现代性承诺,后者曾是中国近现代政治与社会解放运动的基本关切与核心理想。
“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本文于2月13日首发于微信公众号“蜉蝣型幽灵”。)
往期评论:
东方主义,多重“边缘”与审美解放:回顾陈漫事件及其争议 (2021-12-22)
欢迎订阅Matters账号与微信公众号「蜉蝣型幽灵」
ID:gh_ff416309254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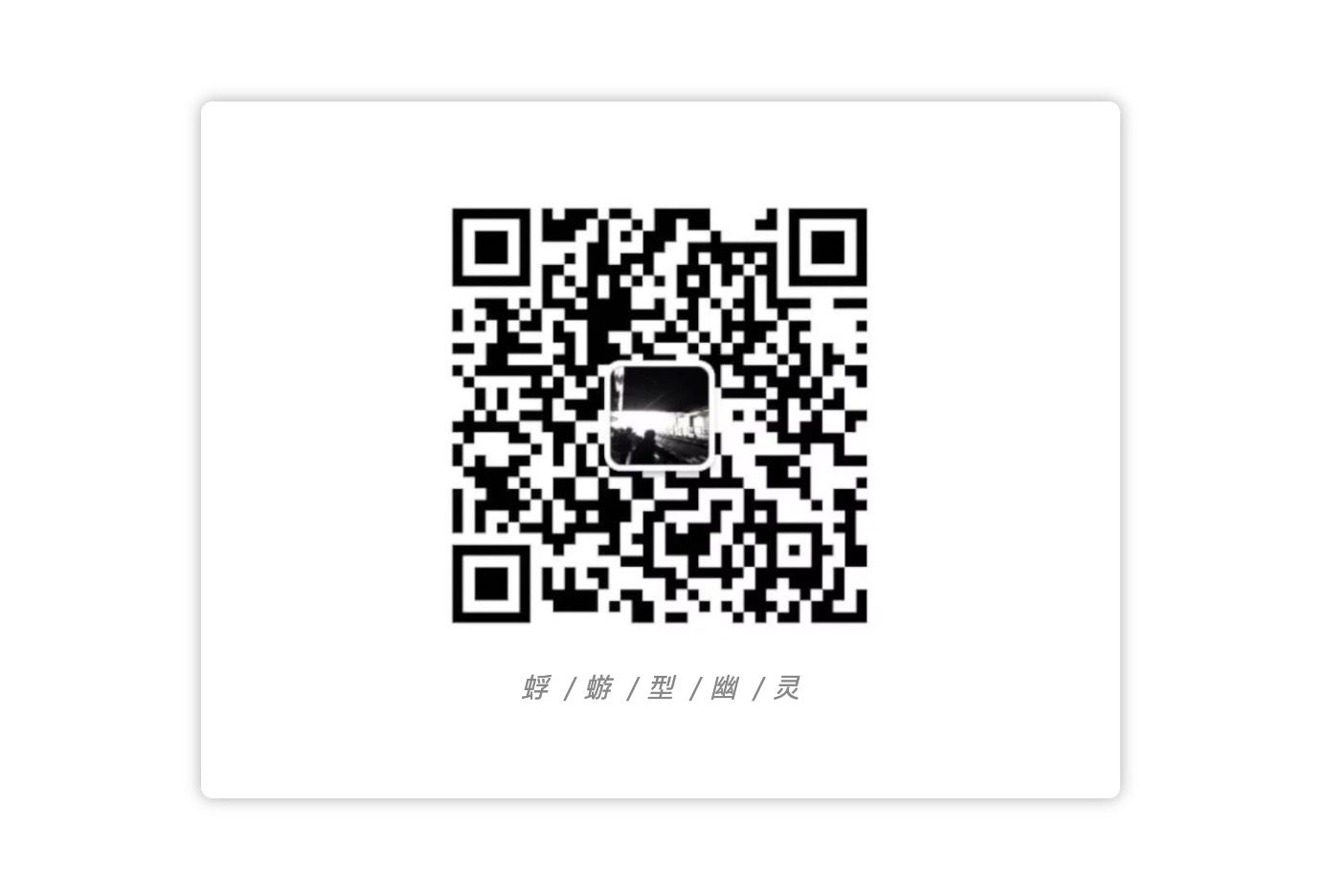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