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割席:自比管宁前不妨从华歆做起
今天跟朋友聊到互联网言论的极化,朋友感慨不少多年好友,因为诸如性别对立、乌俄冲突等争议话题纷纷“割席”。我虽然对生活中的种种“割席”早已司空见惯,但出于某种文字洁癖,始终对“割席”一词近年来在公共讨论中含义的逐渐异化而耿耿于怀。故此作文以记之。
作为典故,“割席”出自《世说新语》: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观。宁割席分座,曰:“子非吾友也。”

上文大意就是名士管宁,不屑与贪慕名利的华歆为伍,愤而割开两人的坐席,以示决裂。《世说新语》把这个故事归于《德行篇》,自然是把“割席”视为品行高洁的象征。不过割席近几年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却出自19年的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期间不乏诉诸暴力的所谓“勇武派”,引发舆论哗然。为了团结“统一阵线”,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温和派也公开宣称与“勇武派”不割席。名为《不割席》的纪录片甚至入选了2021年奥斯卡提名。在这种叙述中,“不割席”俨然成了“同仇敌忾”的正面表达,“割席”则暗含了“背弃同党”的道德谴责,这已与原典南辕北辙,堪称“割席”一词所遭遇的第一重污染。(即便撇开政治,仅从语文角度,我也反对这种有意无意的褒贬错用。如果同情勇武派,那么应该说“不切割”而非“不割席”,“割席”本身内嵌了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

或许是因为这股“不割席”的浪潮,割席一词在近年社交网络出现的频率陡增。网友间寻常的拉黑操作,似乎都得改称为“割席”才能显出一种不言自明的正义感。这是“割席”的第二重污染,即其内涵的庸俗化。这个结论听起来似乎有点突兀,朋友反问道:这种语境下的“割席”并没有褒贬错用的问题,每一个割席者都认为自己占据了道德高地——至于事实是否如此是另一回事,但看起来,似乎没有违背“割席”这个词的内涵?
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既然“割席”实质上只是对社交关系的一种“切割”,那么大家为何偏好用“割席”而非“切割”一词?换句话说,“割席”相较于“切割”的那种道德优越感来源于哪里?
让我们回到管宁割席的那个故事。管宁割席分座,对着同窗华歆说出“子非吾友”时,华歆想必是很难堪的。故事戛然而止,我们无从得知华歆如何反应。但华歆大概是认同管宁所秉持的道德准则,哪怕自己不能做到。原因有很多,例如华歆后来在魏国出任高官,仍极力举荐管宁,对管宁当年的斥责不以为意。其次华歆本身也是一位颇有操守之人,只是比闲云野鹤的管宁多了一份烟火气,如《世说新语》同样记载了一则褒扬华歆的轶事: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以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华歆与王朗坐船避难时,其他落难者想搭船,华歆拒绝。王朗表示既然尚有空位,理应伸出援手。这时的王朗似乎比华歆更具人道主义。不过后来贼兵追上,王朗便想丢下此人,这时又被华歆拦下。华歆表示自己之前的顾虑正是如此。不过既然答允救人,怎能出尔反尔。华歆相比于王朗的优点在于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私心,并不加以掩饰或自我欺骗。在承认不足的基础上华歆不至于陷于王朗一般“伪圣母”的道德困境。这一点也体现在管宁割席的故事中,华歆固然没法像管宁一般对片金熟视无睹,但他捡起来看看后又扔去了;至于围观达官显贵的高头大马,更是人之常情。以“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的道德标准来看,华歆当然比不上管宁一般淡泊,但反而更有一分普通人努力践行道德操守的真实感。
更为可贵的是,华歆承认自己的不足,接受一个把自己置于道德劣势的评价体系。在割席的典故中,人们往往欣赏、甚至自我代入不慕名利的管宁,却很少去想,“割席”的道德优越性之所以成立,需要被割席者的默认。正因为华歆自知理亏,没有多说什么,割席才成为一段佳话。试想华歆如果怒斥Fake News,场面将何其荒唐。
可惜当今的“割席”正是如此。相当于在管宁割席后,华歆说“割就割,老子早就看你不爽了,要割我先割……”如此互割,与小学生在课桌上画三八线互不相让并无本质的区别。当双方都自恃占据道德高地时,道德感本身就被消解了,甚至延伸出一种滑稽的感觉。与其说所有人都是管宁,不如说管宁也被庸俗化了。
小时候读三国,一直对华歆的形象有所困惑。《三国演义》中他是逼着汉献帝禅让的曹魏爪牙;割席的典故里他俨然是个小丑;可《魏略》却记载时人将华歆视为龙头,管宁为龙尾:这么一个趋炎附势的家伙,怎么配位于管宁之上,忝居龙首?后来逐渐意识到,除了演义的抹黑,以及我对华歆的事迹了解有限外,华歆在割席的故事中,或许并不是个丑角。甚至于华歆的闪光点,恐怕比管宁对于如今的“割席大众”更具有指导意义。
年初听到一句话印象深刻:“能够被说服,其实是一种能力。”生活中的大多数人,太害怕自己的观点被驳倒、证伪,仿佛那意味着对自己人格与智力的彻底否定。不少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大V在文章下方禁止留言或仅限粉丝留言,多少也有这种味道。可是,从逻辑上说,想要不被驳倒,何其简单。对任何话题,只要构造一套自洽且不可证伪的话术便能保证在形式上“永不出错”,这对于具备一定的逻辑与语言表达能力的人而言绝非难事。但如此不仅对于增长自己的认知见闻毫无裨益,也更会使人安于一种虚假的坚硬外壳之中,沉浸于自己“不可能被说服”的现实,以及“不能被说服”等于“永远正确”的幻觉中,参与着一场一场的“公共讨论”。或者说,把每一场讨论变成立场恒定的辩论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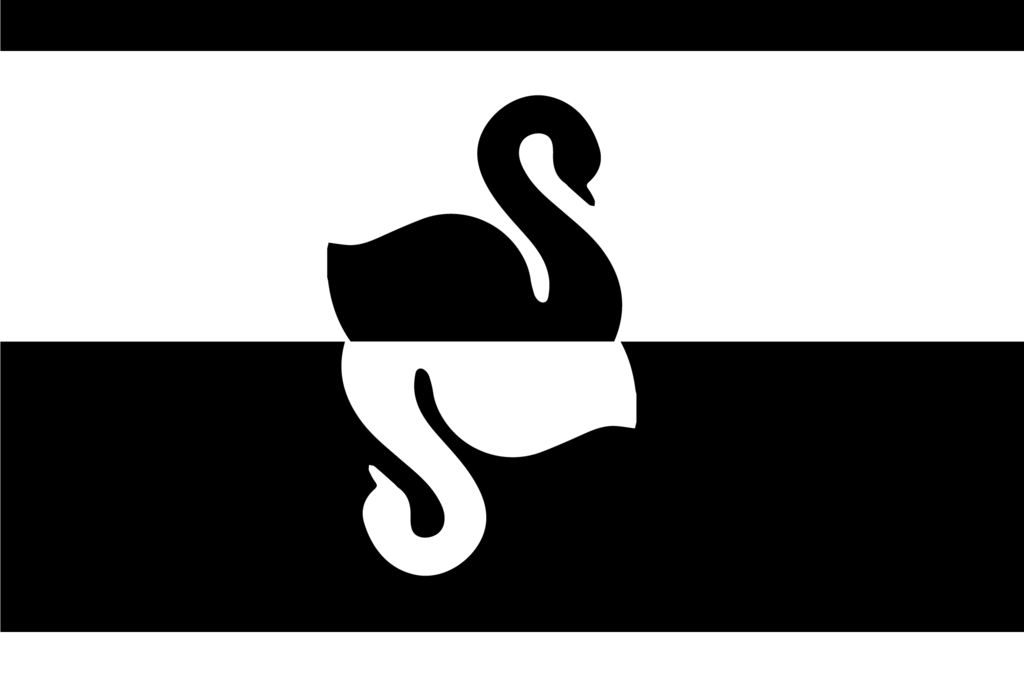
当两位坚守“不可证伪原则”的人对质时,他们唯一的结果就是互相“割席”。割席这个词内嵌的道德优越性,同样营造出一种“正确”的错觉。殊不知,互不相让地“割席”不仅在消解这种虚幻的道德感,也在解构割席这个概念本身。
看起来,人人都想成为管宁而不是华歆。但是倘若没有自知理亏的华歆,管宁也只是空中楼阁。管宁割席的基础,实则是一种对于是非判断、道德标准的基础共识,不以各方立场为转移。这个共识的建立,既需要居高临下的管宁,更需要自承其短的华歆。可惜世上想要割席的管宁多(也许他们最后证明只是王朗甚至王莽);甘愿被割的华歆却少。从这个角度,华歆恐怕远比大部分割席者有着高洁得多的品行与道德追求。
在自比管宁之前,我们或许得先从华歆做起。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