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支流里
在支流里
我在支流里生长成人,我扑打江河湖海的水波,我也踏过世人艳羡的浪,却总放下桨板,游向一条、一条,又一条支流。

在支流里
在支流里
我在支流里生长成人,我扑打江河湖海的水波,我也踏过世人艳羡的浪,却总放下桨板,游向一条、一条,又一条支流。
七日書#4.3|萬火
烟雾里,可以看见一尊印度教的象头神像,静静地伫立在巷道最深处,由万火对面的印度餐厅的人们常年供奉着,香火不断。今天写文章时才特意查了,这是犍尼萨神,智慧与破障之神。不知祂看过多少个与我们一样困惑而迷茫的青年。

上海最后随记02
愿我们以后多享乐少吃苦。

七日書#4.2|像一碗米粉那麼好
一碗米粉常常提醒我,碗沿以外的世界一定充斥着不确定性、误解、争执、伤害、悲剧,但碗中盛着的是确凿无疑的美好,精心腌制过的配菜,用恰好的火候炒出来,放在快速过滚水烫得刚刚好的米粉上,淋上花费真实的时间熬制出的高汤,这是一定会好吃的东西,这是可控的好。

七日書#4.1|「吃是生者的特權,那麼要吃點什麼呢」
食物进入我,我的身体一道一道地处理它,分解它,这亘古不息的能量循环里,暂时留存在此刻的,暂时披覆在这皮囊下的这一段,就是我,我在让它成为我。

七日書#3.6|剑身长度约为一年
我写过这样一句诗,「有些人穷尽一生 / 都在把许多个名字粘合」,然而我觉得央这个名字浸透了痛与血,充斥着我被判为非我的误读与曲解,因此咬牙切齿地要将这名从我身上割断。

七日書#3.4|再陪我走一段
在这个冬天,你的身体发出很多的信号,她要很多很多的休息,她可能暂时不想吃很多东西了,因为你要在冬眠里度过这个冬天。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积极和包容的视角去看待过我的身体现在所处的状态。她说我想身体是有很大的智慧的,她可能更清楚你们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七日書#3.3|泥鏡
穷人家用什么镜?木制三脚盥洗架上有一小镜,几代人的灰尘污垢积累下来,再不能擦净。老窗玻璃粗粝不平,点亮灯光也不能倒映。溪水破碎横流,照不见人脸。穷人能显影自身的,是水稻田灌溉后的泥潭,红不红,黄不黄,一汪泥镜,照得人面色发苦,但不如命苦。

七日書#3.2|當我成為你的女人
这一篇是我第一次用半虚构的方式写作。其实本来想写的并不是这个主题,只是最近现实生活波折满溢,没有太多心力去细细整理思索,而昨晚想起性虐待事件后所有相关记忆就萦绕不散,索性便将这些行为都集结成同一个抽象的人,绛,这世上查无此人,本文并不想控诉任何一个前伴侣。

谢谢你青春
然而 Roxie 就是这样的存在啊,是我们的第一个安全空间,是还没有那么勇敢的我们,还没有那么漂亮的我们,还不敢拥吻的我们,还不敢跳舞的我们,还不知道我可以作为我生活的我们,所得知的第一个也许可以被接纳的地方,也许可以自由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喝下不那么好喝的酒,再一起在走廊用同一个…

失乐园的少女船长
尽管当时的我依然百病缠身、穷困潦倒,像这船帆都碎裂成几缕布条的、甲板破了大洞的、木板膨胀变形的、油漆几乎都悉数脱落的幽灵船一样。然而正如这幽灵船一样,在它崭新出厂时它注定永远停泊在这个港口,也许在躯体腐朽的现在,才能悄悄在夜色里起航。

无家可归的我们向彼此降落
《阿飛正傳》里说的无脚鸟,说得大概就是我们这样无家可归的人,我因我的酷儿性被我的户籍故乡放逐,我的残酷青春让我的父母家无法成为我可以归去的家,我的成长地,我抓在身上的文化符号,终也不是我可以「回去」的场所,然而这世上却有人看见我作为我,有人深爱我正如我深爱ta们,ta们为我照亮一…

残酷青春与天台的困兽与脱兔
卖吧,卖吧,卖掉吧,将这残酷的青春打包,将这债台高筑的痛苦一口气清算,将这创伤累累的往事一口气清偿,我前前后后操办着卖房的事,唇枪舌剑、巧舌如簧、舌战群儒,浑身有股使不完的劲,亢奋得如一只走投无路的脱兔,我要逃,我要跳脱,你们谁都别想拦住我,这世界置我死地,我要把它卖了而后生。

「寄生在这样的平原本不是我的错」
我们果真来自同一片故乡,那么熟练地搬弄着死亡,那么亲切地呼唤着水体,我们就像黄梅天里的水珠一样,无根无凭,无依无靠,悬浮游荡,生活在次要的时刻里,困惑着,困顿着,把无法宣泄的愤怒变成一句句呼唤一般的叹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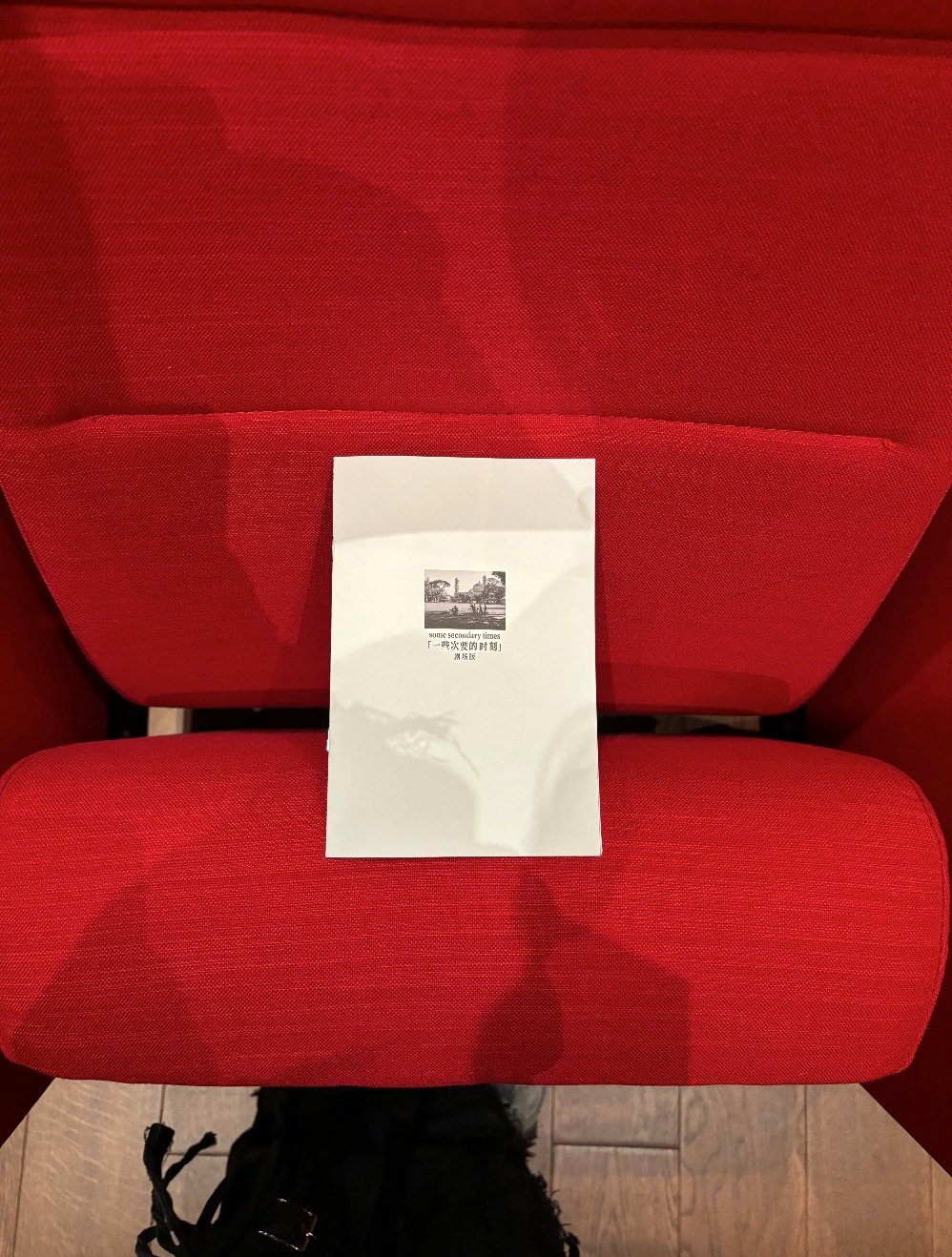
吃着浙北菜长大
寡淡其实是杭州生活的底色,在互联网企业到来前,在那些巨大的赛事、峰会光临这座城市以前,它一直只是一颗明珠,是异乡的人们眼里的天堂,是市民的一座巨大公园,一切宏观的都和我们无关。那些荣耀的、光辉的、蓬勃的叙事,在西湖明镜一样的水波面前无关紧要;那些悲哀的、挣扎的、苦痛的叙事,在西湖绸缎一样的水波里面慢慢溶解。

梯云纵
我总是想,你在纵身一跃的时候,有没有学着那个架势呢?幸存至今的我,竭力开拓了去选择的自由的我,有没有领会「梯云纵」的奥义呢?

在支流里
我生长在创伤遍布却又乏善可陈的支流旁,我早就被赋予了过分纤细敏锐的感知和一颗过分感性的心,我注定会持有大部份人并不认可的价值与理念,我注定会漫不经心地过上与主流世界离经叛道的生活,因此没有什么既存的地缘旗帜或文化空间可以放置我的归属感,只有同样漫不经心、随随便便、轻如片羽的一个缘份,适合被我拿来打成叫做故乡的纽带。

一滴水之王
我立于我的生活,我是我人生的王,我的话语即为权柄,落地就成秩序。

顿点
我写作时很喜欢用顿号。我总是抓紧每一个能用顿号的时候去用顿号,一个顿号的力量让我有点着迷:它不是句子的终止,但却使诵读停顿;它是一种分隔,却意味着相邻的词语彼此从属;它让词从句里解放,单单跳脱出来,释放出最本真的鬼魅与威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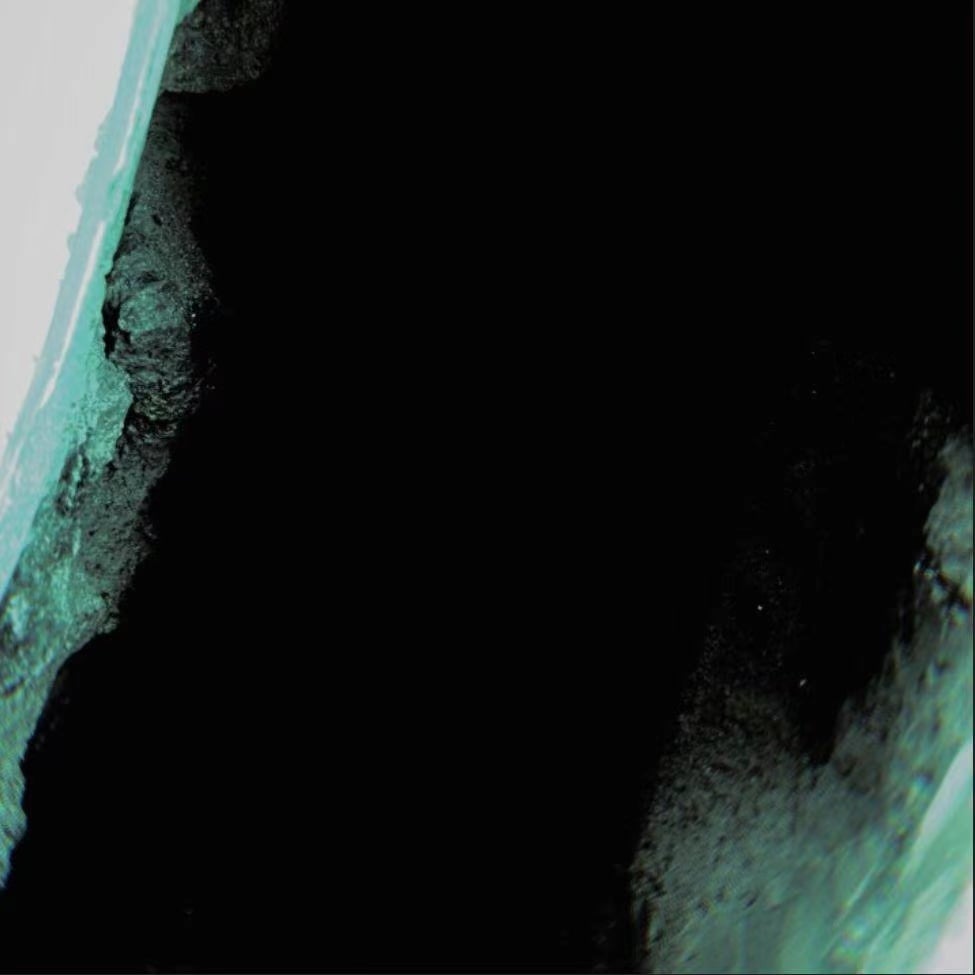
我缺少一个告别词
人们如何告别呢?我开始咀嚼我学过的这些词。

偶尔可以蹲一下
偶尔就是要蹲一下,才能遇到这样次要的时刻,偶尔要把身体折叠一下,偶尔要拥抱自己一下,这是随时都可以做的迷你革命,我们一下子就变小啦,大人的世界就去他的吧。

人物弧光的入射角
在我们各自所折射出光芒的入射角处,还拖着一条幽微的,牵扯自并不悠久但却足够曲折和遥远的,个人历史的曲线吧。

性与同人与我的亡灵朋友
我看过你们的姿态,就也得以偷生。
